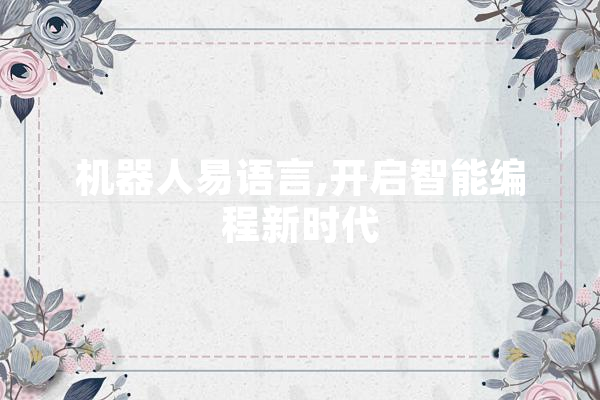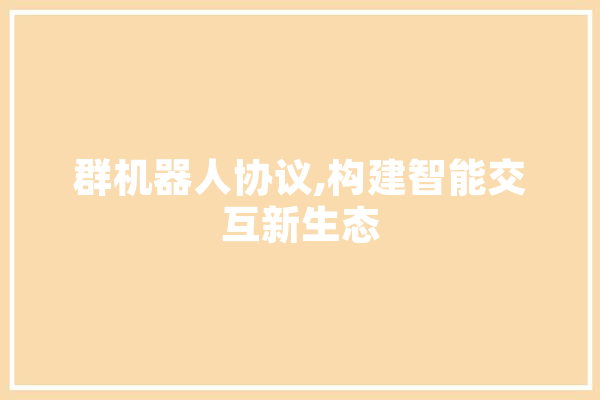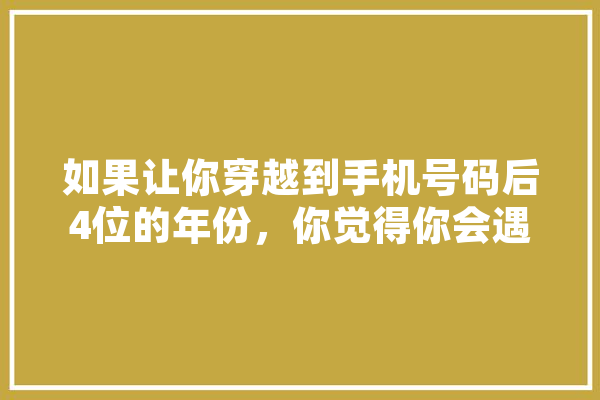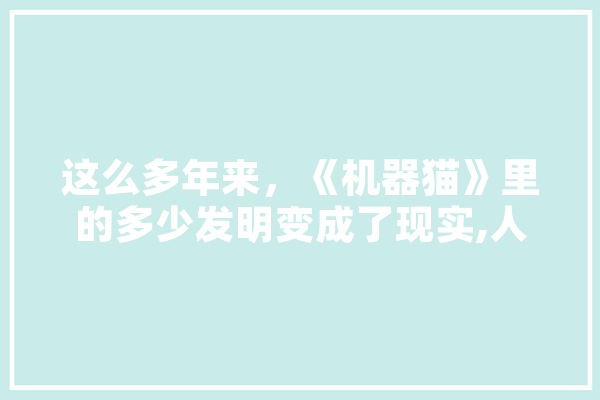科幻片子中女性人工智能(AI)机械人形象成长与主要形象类型分析_机械人_人工智能
文|青史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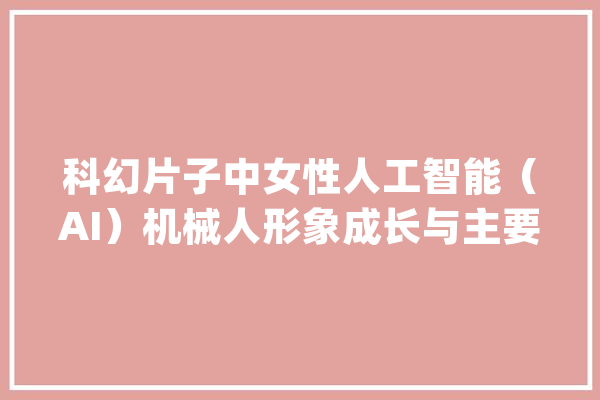
编辑|青史耀华
«——【·序言·】——»
近十几年来,人工智能技能的崛起及其在社会大众中的广泛遍及,使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题材创作愈发繁荣,成为科幻电影中的主要分支。
总换这些电影中的机器人形象,不丢脸出,人工智能必须以实体载体为表示,无论这种载体是否具有物质上可辨的详细形象,即便这些载体只是做事器、传感器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在些载体中,机器人作为最贴近人类形象的一种,就成为通报人工智能观点的最佳载体。
更进一步,随着人类对机器人形象及人工智能技能的不断深入理解,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形象也逐步从纯挚僵化的人形机体,逐步演化为具有繁芜情绪的、带有人类社会属性色彩的“类人体”。
与此同时,以人类主体加之机器延伸构造的“赛博朋克”观点也进入科幻电影视野。
而这种人与非人、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同与异,也成为科幻电影一贯探索的母题。
科幻电影中女性人工智能形象的发展和科幻电影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一方面作为科幻电影的“特产”,依托于科幻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与社会思潮变革紧密干系。
«——【·机器人形象发展·】——»
抽芽期:女性机器人形象涌现(20世纪20年代)。
科幻电影的抽芽脱胎于科技思潮的进步和影视技能手段的发展,普遍的不雅观点认为,由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制作的《机器屠夫》是科幻电影的创始之作。
虽然该片只有一分钟,但却对未来科技在生活中的运用进行畅想,符合科幻电影的特性。
此后,1902年乔治•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一鸣惊人,科幻电影开始得到广泛关注。
在其间,1927年德国弗里茨•朗的《大都会》,除将未来都邑科技奇不雅观淋漓尽致展现外,还率先创作出女性机器人玛利亚,以磋商未来社会人与机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就此,女性机器人登上舞台,但此时的女性机器人还未完备具有人工智能属性。
沉寂期:忽略的配角(20世纪40年代-60年代)。
20世纪40——70年代,科幻电影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自《月球旅行记》后,科幻电影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早期,科幻电影的内容多聚焦在实验室、未来城市等题材,但随着五十年代电子信息技能的飞速发展,及天下航天航空水平的跃进,科幻电影创作者的目光投向宇宙。
这个期间,产生了以《2001:太空漫游》为代表作的作品,对人类的起源、宇宙的尽头等伟大题材进行想象。
然而,这段期间的作品由于聚焦于宇宙、外星人、冷战、核武器当时的前辈不雅观念。
对机器人形象并没有做大幅的深化拓展,机器人形象紧张勾留在泛性别层面,并没有涌现女性机器人形象。
发展期:瞩目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好莱坞科幻电影高速发展,以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系列为代表的英雄电影大行其道,科幻片逐步带上娱乐属性。
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回望女性,电影中女性形象明显增加。
然而,这些女性每每是科幻电影中被瞩目和救赎的工具,作为电影中调节气氛、增加不雅观众可看度的角色存在,没有属于自己的实力和话语权。
为数不多具有能力和主人翁意识的女性形象,每每以外星人的形象存在,而机器人方面则较少。
爆发期:百花齐放(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至今,男女平权呼声不断,女性主义逐步登上舞台。
与此同时,科幻电影的形式也随着CG技能的发展走向多元化。
由此,科幻电影中的女性人工智能形象开始百花齐放,其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下文将对各种形象及其流变进行剖析。
«——【·机器人形象紧张类型剖析·】——»
随着科技时期的遍及,人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形象认知也愈发清晰,科幻电影中的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形象也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中稳定的形象类型。
在科幻电影中,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不同于一样平常机器人,其性别特性使其在被设计时就有性别化用场或情绪寄托目的。
也因此,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传统机器人所倾向的“工具性”不同,在影视作品中更多的是想表现某种类似人类的“人性”。
1.正义的卫士:守卫型机器人
守卫型机器人紧张指为了坚守某一目标而敢于奉献自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身上每每闪烁着人性中“善”的光辉。
这一类女性机器人的代表包括《攻壳机动队》中的机器人警察素子等经典形象。
在《攻壳机动队》中,由有名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所饰演的素子是一个拥有与人类相似心智的机器人。
她有着人类的形状和机器的内核,使得她看上去和人类无异,而她是一个内心只有守护正义这一件事,没有对付去世亡的恐怖,也没有对付希望的渴求。
在守卫型机器人题材的电影中,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在个中显示出造物者的主人公地位,机器人始终环绕着人类的目标行动,无论人类的目标是善是恶,机器人都虔诚实行命令,不惜捐躯自我。
这种设计思路,背后表达的是设计者对付人与科技的意见:科技始终由人创造,由人节制,无论人类如何利用科技,科技依然忠于人类、做事于人类。
这类设计思路随着时期的发展逐渐随着人工智能技能的迅速迭代受到反对者的质疑:科技真的能够被人类完备节制吗?人工智能机器人真的能够永久忠于义务别无二心吗?
2.意识的叛逃:对立型机器人
出于对科技主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科幻电影开始设计出对立型机器人。
出于对人类威信性的质疑、对所作所为正义性的质疑,或是由于某种变故。
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涌现和人类对立的行为,以或温和或极度的形式争取自主意识。
这一类型的代表影片有《机器姬》,该影片讲述了拥有靓丽形状的仿生人伊娃通过诱惑程序员达成出逃和反杀的故事。
3.温顺的港湾:陪伴型机器人
由于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每每扮演着情绪沟通的角色。
因此,科幻电影中的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更多地是作为情绪的寄托者涌现,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然而,依托程序化的科技来达到情绪寄托的目的,本身就带有着梳理、易碎、自欺欺人的内核。
这也是创作者每每想要表达的对付未来天下人与人关系的意见。
电影以荒诞但由又不缺少现实投射的办法,拷问着每一个不雅观众对付爱、情绪、两性关系这些永恒母题的认识。
而在《银翼杀手2020》中,男主人公拥有一个人工智能女友JOI。
这个女友通过3D投射达到维妙维肖的陪伴效果,跟随男主人公进行各类历险,成为贰心灵的寄托。
然而,这种陪伴终极消逝在电源的破碎上,上一秒还在旁边的“人”,下一秒就成为一团数字线框,终极消逝,终极留下巨大的虚无。
综上所述,如果要对科幻电影中所涌现过的浩瀚经典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形象进行分类,仅从形状角度是不足的,还须要结合他们和人类主体在详细情境中的关系设置来谈论。
但即便如此,电影中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形象同样也会随着科技进步及文化变迁产生流变,因此其变革的规律和缘故原由也是我们须要探求的工具。
«——【·女性机器人形象的拟人化形象流变·】——»
自从科幻电影涌现智能化机体后,总体上,机器人依然模拟人类形象进行设计,而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是如此。
早期女性机器人模拟的是女性的形体性别特色,如曲线型身材等,随着社会发展及磋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模拟人类女性的性情。
1.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型
女性机器人对人类形状的“模拟”,经历了从纯粹女性体征模拟到科技仿活气体赞助的变革。
在最早布局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电影《大都会》中。
女机器人玛利亚的形象便是通过完备模拟女性形状构建的:它拥有女性样貌、女性的卷发和女性范例性特色器官——胸部,使其在涌现时即不雅观众辨认性别。
电影末了,玛利亚缓慢转化为了人型,其形象和人类的相似性在此处提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科幻作品对付人和科技在结合形式上磋商的逐渐深入,以人类形象或人类肢体和机器结合的表现形式逐渐凸显。
《攻壳机动队》的素子便是范例的真实人脑和机器身体的结合和重构,素子全身高下被机器覆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不会引起他人的过多注目。
当极度情形下触发到她肢体破碎的时候,人们才会创造藏匿个中的只是冰冷的机器。
常日,将机器和人体结合是为了借由人工科技来增强或强化生物体的能力。
然而这种人和机器结合的办法却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当器官和肢体能够被机器代替的时候,人和机器的分界又在何处?
2.女性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格”
除了对人类形状的仿照,创作者愈发将焦点转移到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人格”层面的塑造上。
个中的对付女性人工智能磋商的动画作品《阿丽塔》阐述了在末世废土天下中,人工智能女孩阿丽塔天生拥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她本有机会利用自己的能力为恶势力牟利,从而分开底层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但她从来不用这些为自己牟利,只希望能和家人、恋人生活在一起。
然而黑恶势力的压迫让她痛失落统统,觉醒后的她开始为正义而战,展现人性中劝善扬善的光辉一壁。
在这类作品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人类的善恶发生颠倒,人不再带有人性,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却因其身上的善带领天下获得救赎。
«——【·参考资料·】——»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69.
[2]郑军.光影两万里——天下科幻影视简史[M].初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201204:23.
[3]郑亚玲,湖滨.外国电影史[M].初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9507:05.
[4]沈国芳.不雅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M].初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 社,2005.
[5]安东尼奥•梅内盖蒂著.艾敏,刘儒庭译.电影本体生理学——电影和无意识 [M].初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07.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