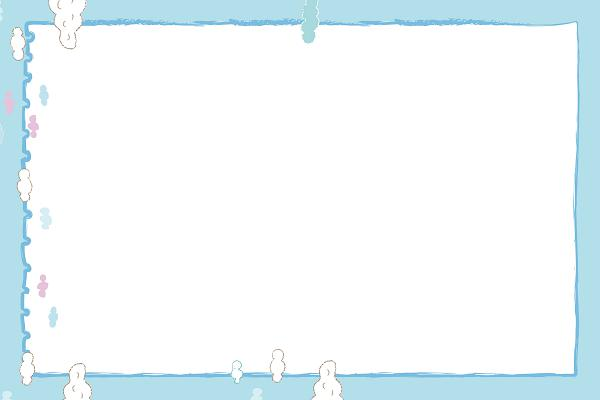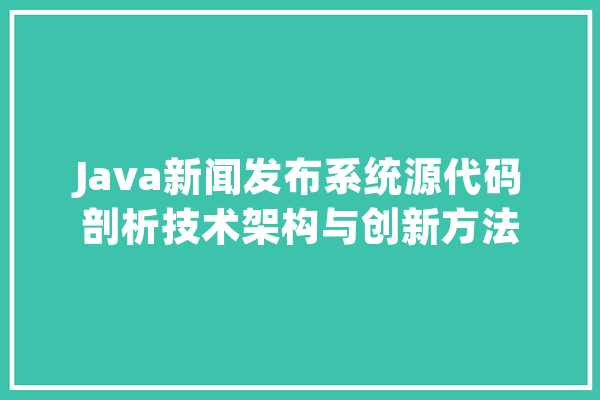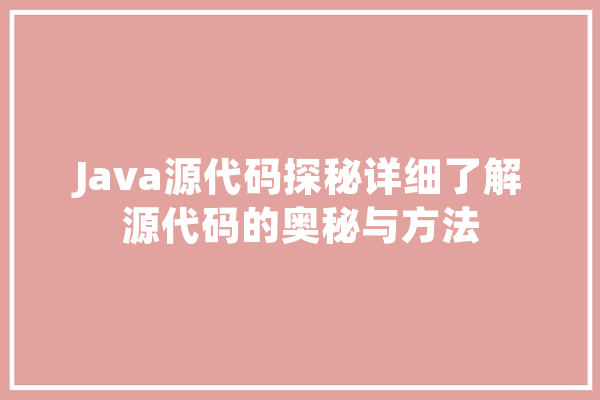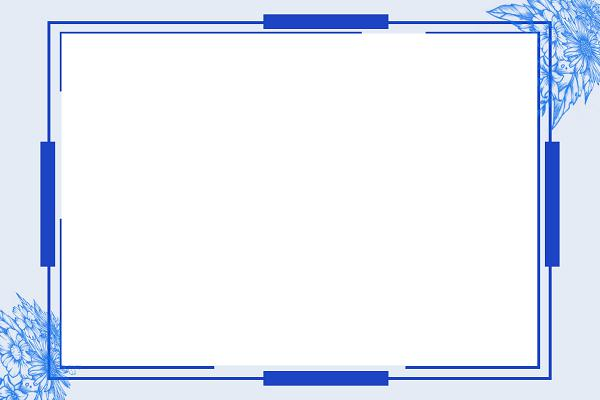刘伟兵:人工智能会实现劳动解放吗_人工智能_技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2期,薛刚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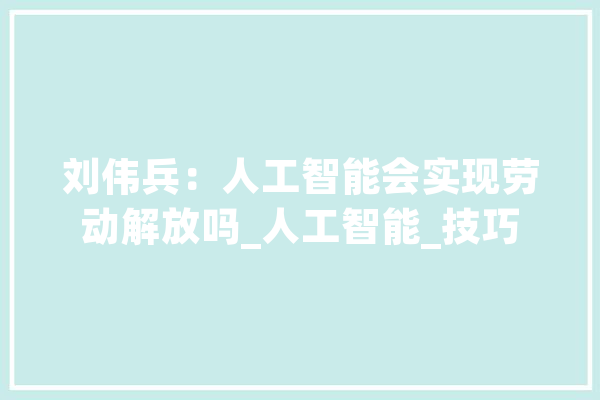
人工智能(AI)会实现劳动解放吗?这是当前各个领域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大多都持较为乐不雅观的态度,认为智能化生产办法的变革抑或是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运用,一定会让劳动者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然后可以去从事自己想从事的事情。这些理论磋商触及人工智能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人工智能纯挚的技能维度,为学界后续研究供应了新的学术成长点。但是,这些谈论大多从详细劳动维度,以免除直接劳动形式的技能层面进行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磋商。这一理论框架在认同人工智能带来劳动解放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人工智能带来“失落业”的惶恐之中。这一“症结”使得我们有必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中,重新核阅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关系。对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劳动解放问题的回答,该当置于劳动解放是何种劳动解放的理论条件下,以深入劳动解放实质的理论进路去磋商。基于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不雅观和剩余代价规律两大科学创造出发,对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劳动解放以及如何实现劳动解放进行磋商。
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解放的把握存在着两个向度:其一是代价性层面,将劳动解放看为难刁难异化劳动的摈弃,是使劳动回归人自我发展本身的过程;其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认为劳动解放便是自由韶光的得到与扩大,是人们在自由韶光中进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人工智能技能的运用,的确在这两个方面都为劳动解放的实现供应了必要的技能条件,而且在事实上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关于未来生产办法的“预测”。
人工智能是劳动解放的技能准备
学界对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技能层面磋商,即认为这种生产办法的变革能够将人类从危险、繁重的事情中解放出来,并摈弃异化劳动,符合马克思对劳动解放的历史条件磋商。换言之,人工智能只是劳动解放的历史条件之一,是劳动解放的技能准备,只是为劳动解放供应可能性,并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更不能大略地将人工智能技能下的“不劳动”等同于劳动解放。
第一,人工智能技能的涌现与发展本身便是剩余代价规律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表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成本的自我增殖便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成本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紧张是通过两种办法:其一是选择减少人为,其二是减少劳动力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会逐渐从生产环节中剥离出来,劳动与生产的分离,意味着相对剩余代价的生产愈来愈依赖于劳动资料的效率。而这种效率则“取决于科学的一样平常水平和技能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这便是剩余代价规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一定会涌现的趋向于“无人化”“自动化”的智能化生产征象,以及一定会出身出可以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和最大限度依赖固定成本的“无人化”生产变革的“马克思预测”。
第二,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供应了固定成本形式和劳动形态上的技能准备。其一,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供应了固定成本形式上的技能准备。学界在技能路径上认为人工智能实现劳动解放的盛行不雅观点因此为人工智能由于技能上的打破,已经成为独立的剩余代价来源,可以让人工智能从事生产劳动,进而通过剥削人工智能的办法代替对劳动者的剥削,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在自由韶光内从事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但是,将固定成本看作独立的剩余代价来源恰好是马克思所要批驳的。以是,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技能准备并不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代价来源,而是形成了一个可以保存代价并能高效率生产利用代价和转移代价的固定成本形式。其二,人工智能技能通过对机器“智能”的授予,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历史样态和组织形式,从而加快了劳动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第三,人工智能全域性赋能的独特代价,触及了劳动解放中的劳动者本身,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为摈弃异化劳动和推动人的自由劳动和全面发展供应了必要的技能准备。
然而,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制,并不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要工人依旧不节制生产资料,那么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工人得到的只能是劳动力价格,付出的却是全体劳动。如此一来,异化劳动就会一贯存在,劳动就无法复归到“自由的生命表现”上来。即便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机器取代人成为现实,但是在私有制不变的情形下,也只会生产出新的异化劳动形式。例如,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技能的发展,人们一些早期的异化劳动形式在生产办法变革中被机器取代了。但是,当代社会涌现了新的异化劳动征象,包括“996”上班模式、居家办公形式、智能监控上班模式等。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战胜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解放。人工智能只是为劳动解放供应一个技能上的准备。因此,为了更加全面揭示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引入私有制观点,在私有制关系中重新衡量人工智能是如何促进有限度的劳动解放的。
私有制条件下人工智能有限的劳动解放
劳动解放的科学路径是自由韶光的得到与扩大。人工智能技能的发展,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必要劳动,从而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劳动韶光也便是剩余代价。那么,可否就大略地认为人工智能技能的利用就一定会让人们免于异化劳动,得到更多的自由韶光,从而实现劳动解放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要放在私有制中的成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答案。
第一,人工智能的利用和劳动的“免除”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这虽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却是以能否得到剩余代价作为条件条件。以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能否利用人工智能来促进劳动解放,要受成本增殖的规律所限定。大略地认为人工智能技能涌现就会一定促进生产办法变革,促进人的劳动解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抱负。
第二,即便人工智能技能被利用于生产办法变革,但是在私有制条件情形下,人工智能技能所节省下来的剩余劳动韶光,也不一定会被劳动者得到。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智能机器的利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得到自由韶光,反而是试图将剩余韶光转化为剩余劳动。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商品交流规律承认下的成本家与工人环绕自由韶光的权利之争征象,只有工人阶级具备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从清闲阶级走向自为阶级,才能具有阶级力量,与成本家进行自由韶光的争夺。
人工智能时期一方面存在着促进人们自由韶光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将自由韶光转化为剩余劳动的剩余代价规律。如果忽略了阶级成分在促进自由韶光转化方面的浸染,而仅仅寄希望于科学技能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时期悖论下,就意味着寄托于人工智能实现劳动解放的设想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第三,即便劳动者得到了剩余劳动韶光,也不一定会将其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韶光。这是由于,成本在追逐剩余代价的过程中,客不雅观地促进了消费的全面扩展,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人们新的须要,个中很多都是虚假需求。人们在自由韶光里,看泡沫剧、逛街与购物,消费着自己空余韶光的同时,也消费着由成本全面扩展带来的全面生产。如此一来,人们虽然从生产环节中被解放出来并得到了自由韶光,但是在消费环节又使得自己的自由韶光以消费的形式被成本霸占了,从而帮助成本完成自我增殖的闭环。因此,抛开成本逻辑来单独看待科学技能的发展随意马虎造成片面的乐不雅观。马克思就很清晰地认识到,机器生产本身有利于人的解放,但是被成本主义运用后,就会造成诸多悖论性问题。
以是,在成本还是必经的历史阶段中,人工智能技能的利用与否以及对劳动解放所供应的技能准备都是有限的,受到成本增殖的限定。人工智能只是劳动解放的一个必须的技能条件,而且在私有制条件下只能实现有限度的劳动解放。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