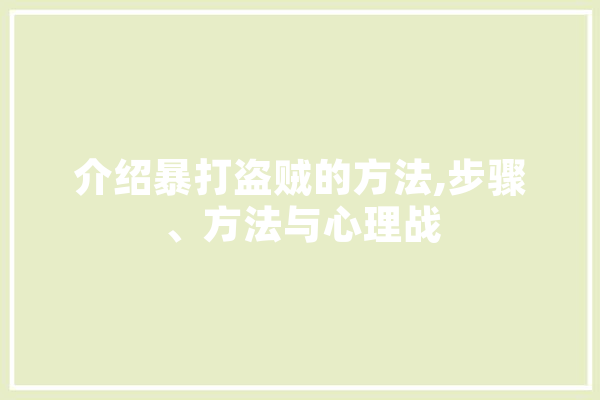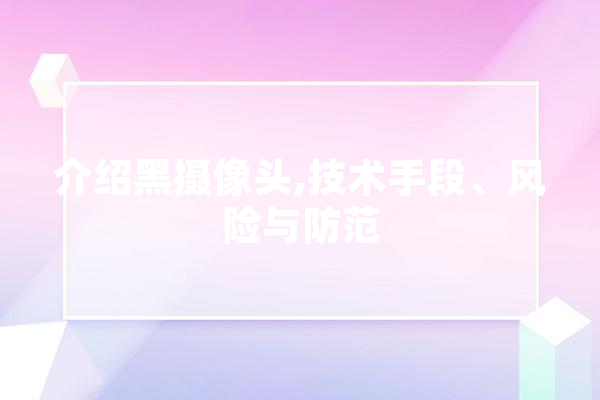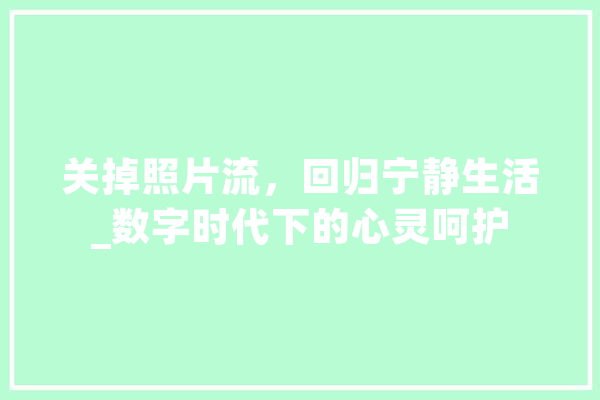人工智能有助于文学照亮人道_人工智能_人类
人工智能微软小冰于2017年5月出版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革。反而是微软小冰写过的两篇高考作文,虽然语句大略平淡,但是涌现了“我”、涌现了抒怀主体,让人感到颇为玄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机器在仿照人类思辨与情绪方面,基本达到了一样平常初中生的创作成果。“它”的存在便是仿拟本身,是一个谎话,它所言说的统统都来自于仿拟。人工智能除了没有主动去做“仿拟”的动机之外,在技能上它已经有能力供应现实天下的表象,包括人类思维和情绪的表象。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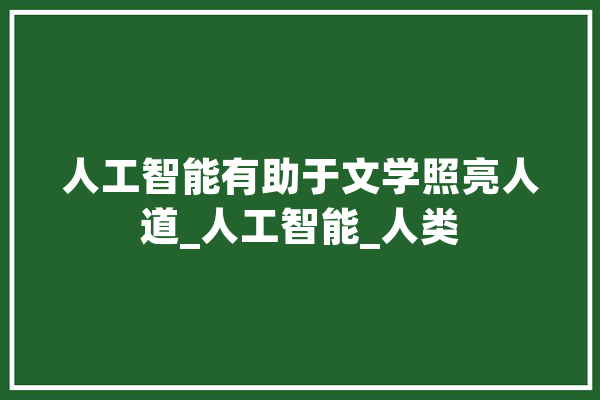
微软“小冰”在绘画。新华社发(任超摄)
虚构文体,在技巧性处理叙本家儿体的情形并不鲜见。比方叙本家儿体是一个跨性别者,可能情形还更繁芜,魔术般地进行虚构和想象,是当代读者感兴趣的话题。虚构艺术的伦理提醒我们创作者须要处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虚构?
我的一个基本不雅观点是,小说紧张处理希望的问题。什么是希望呢?便是规训的问题,例如贪嗔痴。好的小说能够发明新的希望,如《西游记》中的“齐天”之欲。孙悟空走出花果山,是由于花果山不足好吗?显然不是,是由于他怕去世,他对生之有涯感到恐怖,他对安逸的生活感到莫名的不知足。小说照亮了他的这种“不知足”,生发了后续的故事。他要战胜去世亡,战胜去世亡之后,依然以为不放心……听故事时,读者抱着好奇心,看看小说人物如何引领我们走向现实天下很难处理好的问题。这是我们创作最初的目的。虚构是知足我们修正天下的希望、以想象驯服天下的办法之一。以是,人工智能的希望是什么呢?
人工智能虽然不具备渴望生发或战胜本能的动机,却可能有办法帮我们照亮现实天下中被遮蔽的人的需求。有学者见告我们,人类情绪并不是一种分外的存在。机器除了超越解放生产力的单一工具性,还可以精准为人类办理情绪需求。2013年的电影《她》,就以艺术的办法呈现了孤独的人类对付机器的情绪依赖。这样包裹在科幻外衣之下的爱情故事,实质依然是一个伦理问题:科技到底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变好了还是变糟了。一个可以想见的答案是,都邑人变得越来越封闭,当下的疫情更加剧了这一情形的发展。科技看似为沟通供应了便利,以至于人们开始躲避真正的情绪打仗。
如果说十年前,人工智能与情绪的联结多有浪漫化的方向,随着时期的发展,如今的我们已经可以在现实天下看到相反的返乡。令人感到恐怖的事实是,我们可以从社会新闻上看到,当智能家居逐渐普及时,家庭关系、恋爱关系也在涌现变革。“暴力”的形式变得更为丰富。
纽约时报已经有过多次宣布,内容是受害者们创造家中的热水器、中心空调温度乍寒乍热。过了一段韶光,她们才创造自己遭到了“高科技家暴”。
据《钛媒体》宣布:“近年来受到智能家居家暴的女性溘然开始多了起来,她们的共同点是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家中有大量智能家居设备,但她们自身对付科技产品险些一无所知,生活环境就完备被掌控了智能家居设备的另一半所节制。”以性别与科技的社会学角度来研判,“以往一个家庭空间中家电掌握权力是很分散的,但有了智能家居,节制动手机端掌握权力的人就可以实现远程掌握家电。安装者乃至可能拥有绝对的掌握权。很多女性都对这些产品不太熟习,这就让掌握权更加集中在男性身上。以往艺术作品里常常会涌现男性惹太太不高兴,太太以不做晚饭来惩罚的情节。恐怕从今往后要颠倒过来,涌现男性用智能家居报复太太的情节了。”以是,人工智能本身虽然不具有主体性,可是它参与人类生活尤其是情绪生活的办法,是当代现实主义的新话题。也便是说,人工智能在文学中的呈现,是可以去科幻化的。它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可能在未来影响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它不一定令我们感到更幸福,反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繁芜。
人类情绪之以是会以艺术为容器加以重铸和再现,个中一个主要缘故原由便是人类具有相互感知和相互理解的能力。作家的共情能力又会高于普通人,会引领自己的读者体验其他人的繁芜处境,天生较为繁芜的艺术共情。但要真正做到“情之以情”是很困难的,好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已经可以试图借助机器的帮助加以实现。
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内容是关注人的日常履历,并从中找到真正的神性,开凿出一个与现实天下不尽相同的精神天下、审美天下。机器显然不会主动带领我们去开拓神性的边界,但这是一种强势媒介,帮助我们照亮人性,照亮人与人关系的困境。新旧环境的冲突总是混乱、虚无的,机器不纯挚只是为我们营建更好的生活而做事,它会滋扰、磨练、暴露我们,并创造新的心灵压抑。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探寻到共情的新形式,命名人类超越原始希望之外的新的渴望,发明新的觉得构造,那么它就不该让写作者感到威胁和恐怖。
潘公凯师长西席曾谈到科技与艺术的关系。科技是求真,艺术追求的反而是不真。这种“不真”我想也不是一种“假”,而是不断翻新的“镜花水月”与“笔墨表征”,其背后的根本,依然是艺术家如何看待人的问题,人的困惑、人的苦楚、人的高尚,人的幸与不幸。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这个时期照亮这些“人的解答”,那么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其他艺术门类,都算是一种有代价的批驳性瞩目。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9日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