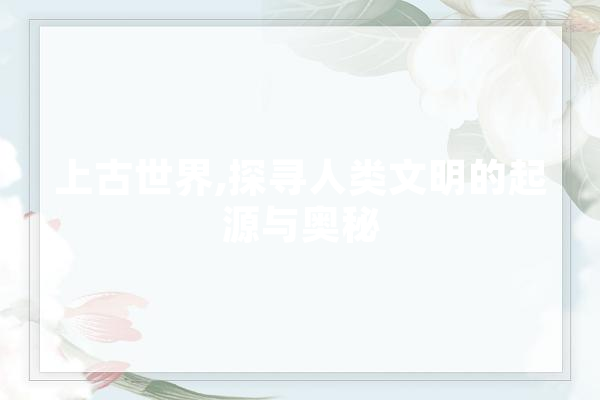主体照样对象——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_人工智能_人类
人工智能的争议正在急剧升温。这个话题汇聚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相互交手的最新内容。人工智能代表的科技逻辑开始尖锐地寻衅人文领域的传统边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已经分别表态回应,表示抵制、戒备或者收受接管。作为这个话题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将为文学艺术带来什么?思想探索饶有意见意义地展开,然而,结论的严明性将会很快超出猎奇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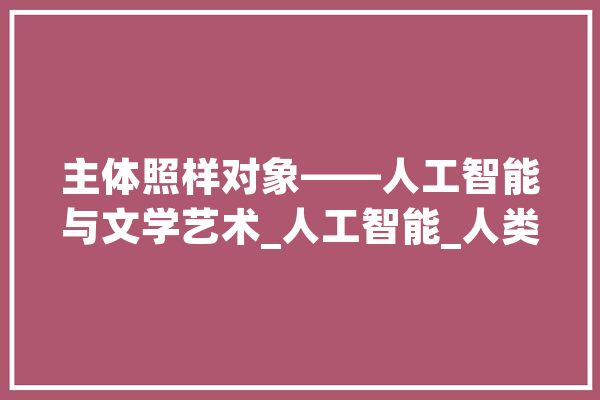
人工智能对文学艺术领域参与业已构成一个能干的事实。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落了玻璃窗》令人震荡——一些诗歌揭橥于互联网,险些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人工智能的作品。相对地说,新闻稿或者侦查小说的基本模式远比空灵的诗歌清晰稳定,人工智能可以娴熟地驾驭它们的“叙事语法”。人工智能绘画与作曲的已经屡屡见诸媒体,一个小视频曾经在互联网广泛流传:人工智能操纵的机器臂写出具有相称水准的书法作品。犹如自动驾驶、疾病诊断或者不同语种的翻译,文学艺术领域的“失守”指日可待。一些人对各种惊悚的预测抱以心不在焉的嘲笑:刚刚爬到树上,就要宣告开始登月之旅吗?另一些人的表情更为严厉:低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率可能产生严重后果。阿尔法狗击败围棋冠军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险些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天的降临竟然如此之快。
人工智能的参与在文学艺术圈制造了持久的喧哗,各种不雅观点错杂交叠。欣然接管人工智能的作家不多,反对人工智能的不雅观点指向不一:一些作家认为,人工智能的作品低劣粗陋,人工智能的“算法”无法企及幽深的精神天下,那些电子元件或者集成电路怎么可能体会奇妙的韵味或者奇特的艺术风格?工程师的设计与墨客的想象不啻南辕北辙。另一些作家感到,人工智能搪突了人类的肃静,这些机器拼凑出来的作品不仅无可称道,而且包含了轻渎文学艺术的意味。
然而,没有情由唾弃人工智能的作品质量。从韵味、风格到颠簸的意识轨迹,人工智能可能在模拟的意义上给予精确的再现。稽核过阿尔法狗对弈的棋谱即可创造,人工智能可以自若地处理奇妙的权衡、关联,以及各类起伏、迂回、呼应。如果阿尔法狗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投入文学艺术范畴,复制大师的水准并不困难。纵然现今的作品尚未达标,未来的潜力无可疑惑。因此,问题的真正焦点毋宁是,我们是否接管这统统?
常日的不雅观念之中,科技以工具的面孔涌现。时至如今,我们不再谢绝科技工具供应的各类产品——我们并不反感烤箱烘焙的面包、电磁波转换的电话语音或者电子望远镜显现的迢遥星空。犹如种田、捕鱼或者建筑房屋,文学艺术同样依赖一套基本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意图,例如画笔、刻刀、颜料、音响器材、电影屏幕,如此等等。没有人由于这些工具的存在而对油画、雕塑、电影或者电视剧感到恼怒。相对地说,只有人工智能供应的作品令人嫌恶。这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或许正好由于人工智能有如此强大的模拟乃至再创造功能。从最初的创意到符号组织的技能完成,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地节制艺术生产的全部流程。神秘的灵感,飘忽不定的想象,呕心沥血的措辞考虑,扣民气弦的悬念和热泪长流的结局,如此繁难的事情竟然一挥而就。那些芯片和集成电路长驱直入,轻松地摘取作家、艺术家的桂冠。这个意义上,工具的观点遭到了动摇。工具仅仅参与艺术生产的某些环节,严格地屈服作者预设的总体主题。工具的一个基本含义即是服从人类,而不是替代人类。然而,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开始威胁人类的主体地位。作家的排斥或容许以追溯至某种潜意识:戒备人工智能涌现太阿倒持的哗变。
当然,至少在目前,僭越的迹象并未涌现——人工智能仍旧循分地驻留于工具的范畴之内。对文学艺术来说,人类的美学标准仍旧表现出无可比拟的威信,决定文学艺术是否合格。不论人工智能配备多么精彩的禀赋,它无法在美学的意义上重新设计文学艺术。
美学是人类历史的分外产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布局”的不雅观点。他指出,动物只能狭隘地按照“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肉体须要支配全部的生产目的;相对地说,人类“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美的追求积累了人类精神的真正高度。相对付动物,美是人类从一定王国跨入自由王国的象征。当然,稽核文学艺术内部涌现的各类美学不雅观念,必须详细地联系分外的历史期间,联系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评论辩论“温顺敦厚”的“诗教”,不涉及先秦期间的儒家思想显然无法完全地阐明。评论辩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兴盛,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的文化潮流是必不可少的注释。总之,美学不雅观念、美感和审美形式有机地镶嵌在人类历史之中,并且跟随不同期间的生活实践而持续地起伏演化。从古老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到“人的文学”,文学艺术和美学标准本身即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
显而易见,人工智能不可能享有人类历史。这决定了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附属地位——人工智能的各类功能以模拟为内在界线,人类是它们模拟的终极偶像。人工智能承认美是人类之间彼此互换的内容,它的任务仅仅是逼真地仿造:人工智能供应的文学文本保留地隐含着作者证明了人类的主体地位。论证人工智能工具性子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一个有趣的例证: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影象功能,但是它不会回顾。“此情可待成追忆。”回顾是文学的惯用题材,无论是朱自清《背影》这种短章,还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巨著。人工智能无嗔无喜,它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溘然回顾动身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的机缘。换言之,人工智能无法独立地产生相似于人类的文学艺术。
阿尔法狗的围棋对局显示出完美的攻防打算,但是,这统统仅仅实行一个大略的指令:赢棋。阿尔法狗对付超出棋局胜负的各种情节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不论是李世石的高慢实足、柯洁的绝望哭泣还是它的得胜赢得的奖金捐给了哪些机构。高超的影象、打算、剖析、综合、研判,粉饰了这个特色:人工智能是一个贫乏的主体。
从事文学艺术时,人工智能无法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它只能追随人类的美学标准,而且从未改变被动者的角色。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显现出独立的美学主见,例如褒扬李白抑低杜甫,或者主动卷入现实主义与当代主义的辩论。这些故事源于人类历史,人工智能只能站在一边充当袖手旁观的角色。
人工智能供应了优雅的诗作或者令人惊叹的绘画,然而,这是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自身丝毫不须要这些美学的抚慰。作为工具,人工智能竭力完成任务,同时无法意识到任务的完成对付自身的意义。人工智能并未形成“类”的实质,更不存在独一无二的“自我”,因此,这种问题形同虚设。
然而,这种状况必须附加一个分外的韶光状语:“目前为止”。事实上,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乃至科学家担心的正好是,情形可能发生变革: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汇聚为一个“类”的共同体,并且产生自主的希望,如果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巨大的危险可能迅速附近。这并非无端的忖度。相似的事情已经在人类身上发生过一次了:人类的“自我意识”显然形成于进化的中途,只管突变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清晰的描述。
另一些议题环绕于“后人类”的观点周围。生物医学技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已经展示了这种前景:一些以人类为范本的人造生物指日可待。这种人造生物须要什么,讨厌什么?那个时候,人工智能或者“后人类”的美学标准可能迅速出身。但是,文学艺术的竞赛或许不再那么主要。人类即将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如果它们成为人类的对手,这个天下会发生什么——既然这个对手的各种能力可以碾压人类。
当然,这些辩论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范畴,但是,文学艺术正在给予充分的展现——许多科幻电影正在从不同的视角探索这个主题。没有情由大略地将影片之中的忧患感情视为神经质的杞人忧天,这些作品更像是科学主义强势崛起诱发的一系列文化症候。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5日14版)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