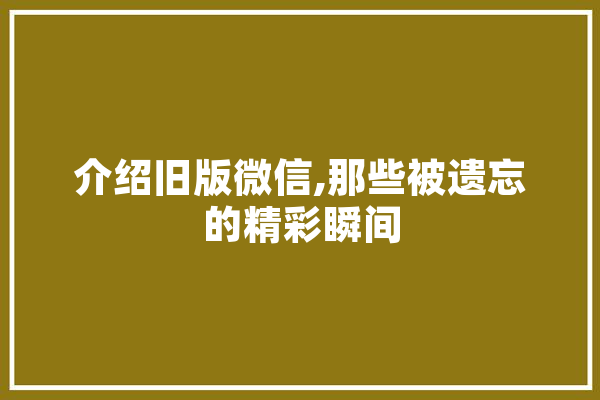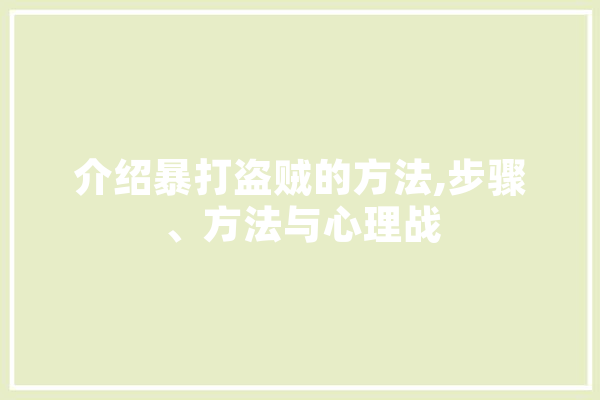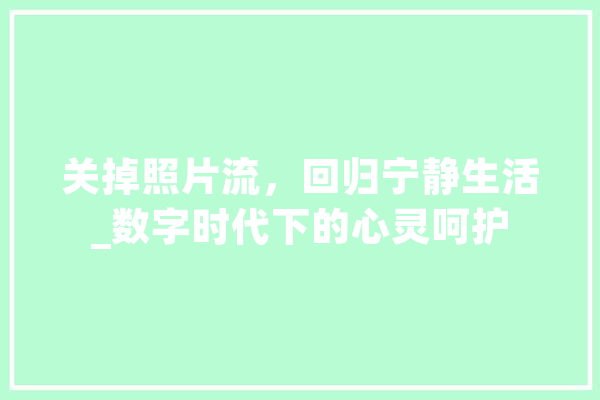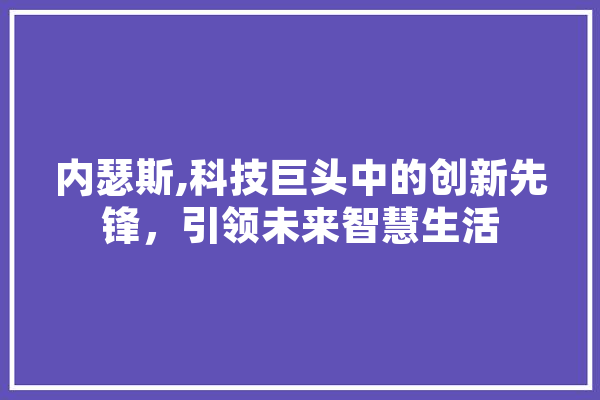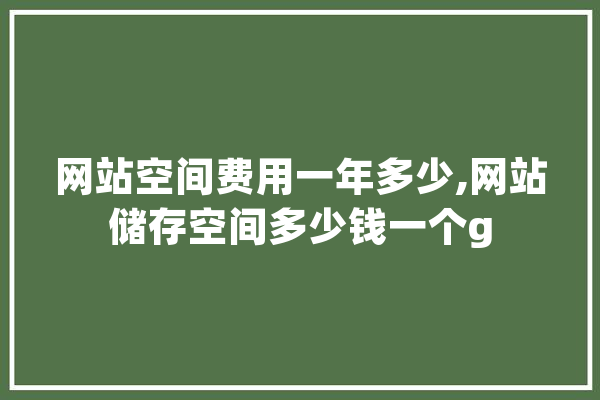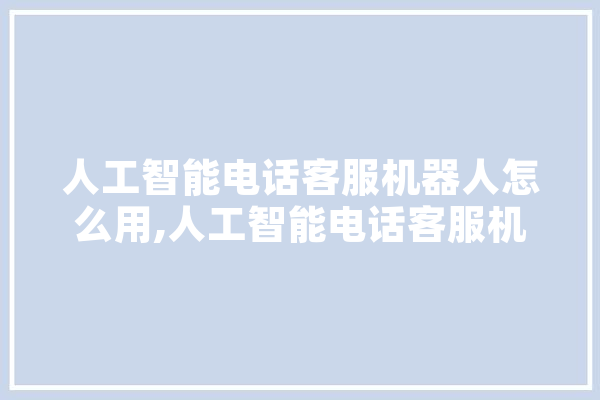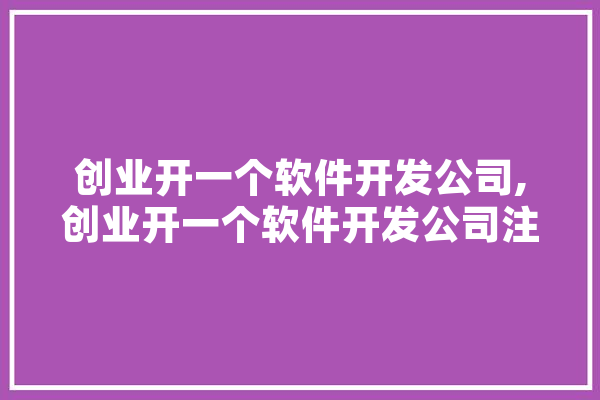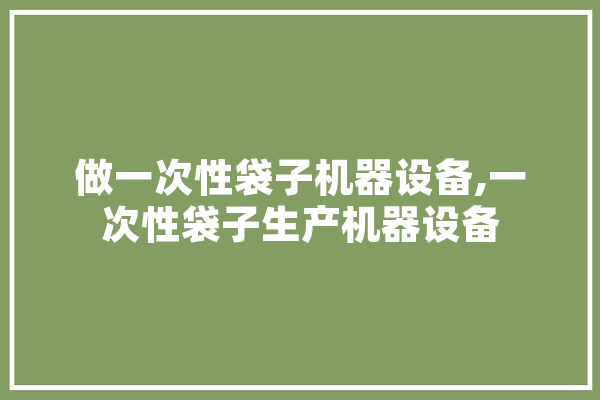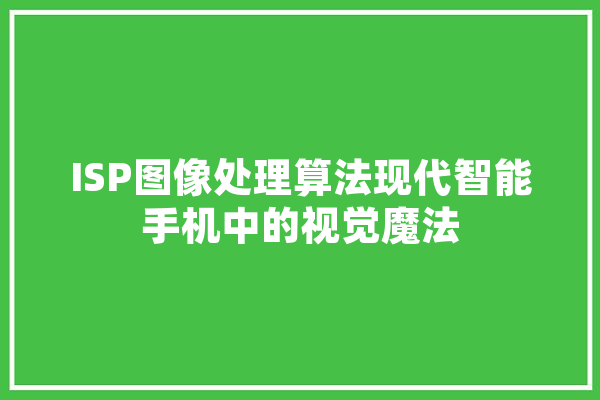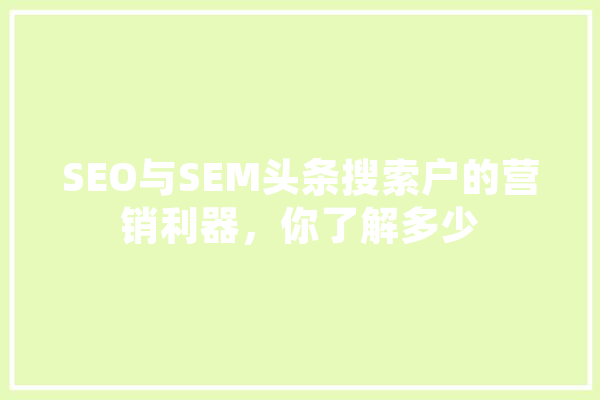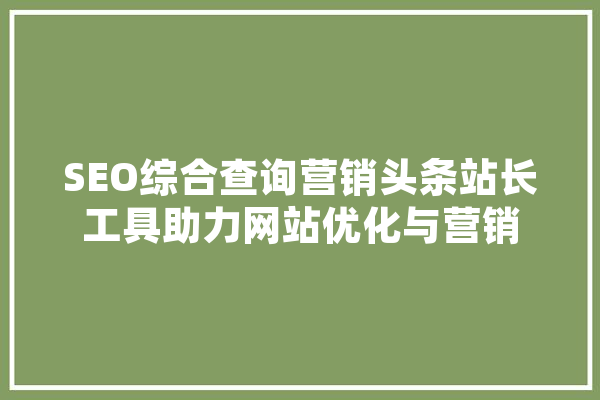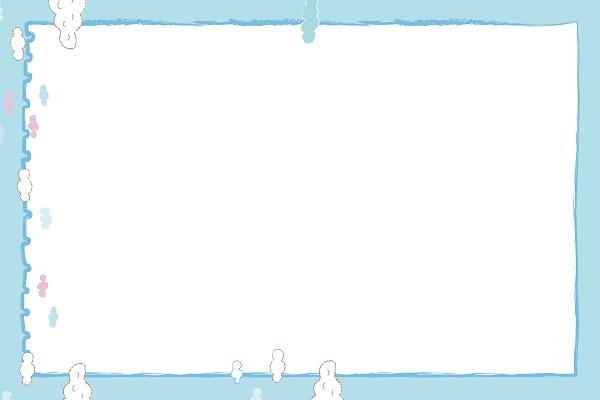【专访】英国哲学家伊莎贝尔·米勒:把人工智能视作女性化的原始力量_人工智能_米勒
界面***编辑 | 黄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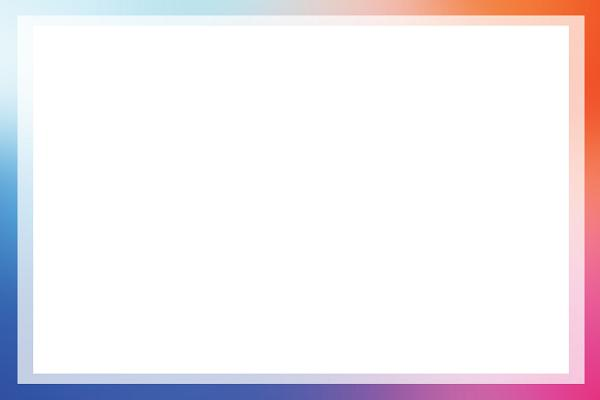
十年前的电影《她》(Her)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离婚的单身男子与一位拥有迷人声线的机器人相恋,他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他完全的爱情,并逐渐希望能与她——一个并不真正拥有肉身的对话机器人——做爱,就像常日的亲密关系那样。但他逐渐看到了“原形”:作为一个拥有繁芜多线程处理能力的机器人,她逐日在与他互动、恋爱的同时,还与其他成千上万个人互动和恋爱。
英国哲学家、精神剖析学者伊莎贝尔·米勒(Isabel Millar)留神到了这部电影中的张力:如果人类与机器人相恋,除了人与机之间的张力,是否也存在性别之间的张力?精神剖析学的核心观点——性(sexuality)、欢愉(enjoyment)等——在个中扮演何等角色?对付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投射了人类若何的自我意识?
米勒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写成了《人工智能的精神剖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书,于2021年出版。对她来说,谈论人工智能问题的出发点该当是欢愉——或用精神剖析术语来说,“原乐”(jouissance)——一个源于法语的词汇,字面意思指原初的享乐。原乐是精神剖析的核心理念之一。米勒认为,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该当首先谈论“它享受吗?”(“Does it enjoy?”)。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去谈论,人工智能是否有感想熏染和意识、是否存在性别、是否会取代乃至毁灭人类。
界面文化日前在阿姆斯特丹专访了米勒,从精神剖析学视角核阅了堪称时下最热门话题之一的人工智能。米勒认为,人工智能更长于模拟人类了,但并不虞味着它有知觉能力。她虽然研究人工智能但从不该用ChatGPT,由于机器可以仿照的东西并不具有真正的原创性,不值一用。她也提醒我们把稳,当前主导人工智能家当的驱动力是极其男性化的、与成本主义同构的,但人工智能实在有着非常女性化的力量。而面对加沙冲突,当前这个天下多出的一大隐忧,便是人工智能的它与工业战役机器的同谋。
01 认为技能只朝一个方向发展,是对人类思维的狭隘想象
界面文化:你为什么会对利用精神剖析方法研究人工智能感兴趣?
伊莎贝尔·米勒(以下简称米勒):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研究了技能问题、生命政治问题和身体管理问题,研究了米歇尔·福柯、德勒兹、阿基里·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等人的作品,这些学者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根据身体的欲望和潜力来管理和掌握身体。当我进一步深入研究时,精神剖析变得更加主要,由于我创造有关人工智能的文献中彷佛存在某种分裂:一方面,传统哲学方法涉及与原乐、身体、措辞有关的奇妙的问题时批驳性不敷;另一方面,精神剖析领域与人工智能在观点等新问题上并没有太多互动,比如人工智能如何与人类作为主体领悟,如何提出一些寻衅精神剖析根本观点——比如驱动力、无意识、措辞——的新问题。如果我们对“智能”的研究都尚未完善,要理解“人工智能”就无从谈起。
界面文化:精神剖析学说的核心不雅观点之一是,相信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理性的希望而不是理性的思想决定的。但我们本日谈到人工智能,方向于认为它由一整套编排完善、计量精确的代码构成,是理性打算的某种极致表示。在将精神剖析用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在这上面的抵牾?
米勒: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互助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与这个问题有关——试图驾驭人类科学主义理性思维的启蒙思想大方向,是如何陷入持续不断的辩证法之中的?为什么总是朝着某个文明的方向提高,但总在某个点上跌倒并回到野蛮状态、回到恐怖的非理性的冲动之中?阿多诺指的是纳粹德国,形式化和官僚化的思维办法如何造就了这个极度反人类、毫无人性的去世亡机器。
《启蒙辩证法》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办法的核心。我们想象这些技能永久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是对人类思维的广泛性和繁芜性的一种极度刻板、盲目和狭隘的理解。人类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它被各种悖论和可能性所分裂,不能被大略窄化为工具性。关于人类思维的统统都是繁芜程度指数级上升的抽象观点,抽象起源于某种东西的缺席,某种人类试图表现出来的“非存在”。这是活体和去世体之间的问题,抽象可以证明事物去世后仍旧存在。关于“不去世”(undead)的想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之一,我们授予了它巨大的权力,却不明白人工智能实在只是一种抽象的机器,它将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界面文化:你在前不久举行的阿姆斯特丹G10论坛的演讲中提到,关于“原乐”的问题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互动的出发点。在你看来,为什么“原乐”问题对付理解人工智能来说如此主要?
米勒:“原乐”是精神剖析研究的核心,它是一个非常繁芜的观点。它关乎我们对付驱动力(drive)的理解。对付精神剖析来说,常见的驱动力包括弗洛伊德提出的口腔驱动力和肛门驱动力,此外还有视觉和听觉。这些驱动力与原乐密切干系,是我们如何理解人与自身的关系、智力与理性之间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此根本上,我们才开始理解,人工智能本身便是与这些驱动力相结合的,它与我们窥淫癖的冲动、主宰环境的冲动相结合。除非我们理解它作为驱动体与我们互动的办法,否则我们不会真正明白人工智能的潜力。我指的是,它有潜力管理我们,让我们感想熏染到情绪,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消费,让我们产生某些希望。这些形式的原乐无处不在,存在于我们与每一种技能互动的过程中。更详细地说,它们存在于那些被开拓的技能背后的原乐模式中,掌权者正在按照特定的原乐模式行事。
02 将人轻易更换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象
界面文化:根据你刚才谈到的不雅观点,理解人工智能须要从原乐的观点出发,能否举例解释,在空想的情形下人类该当如何与人工智能互动?
米勒:目前人们对付人工智能只有一种非常敷衍的理解。我在2021年写完《人工智能的精神剖析》一书之后创造,不雅观察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预测非常有趣。
自ChatGPT和DALL·E(编者注:一种基于措辞的人工智能图像天生器,可以根据文本提示创建高质量的图像和艺术作品)等人工智能产品2022年问世,我不雅观察到:第一,从政治经济层面来看,人们开始担心许多事情被取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悠久的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第二,从美学和艺术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得到模拟人类创作的能力引发了许多伦理磋商。
以DALL·E为例:多年来艺术理论的研究者一贯在评论辩论“什么是艺术”,当代艺术理论是一个不断质疑自己的存在代价的领域。有人说艺术该当创造一个“不易制造的俏丽物体”,那么落点该当放在“不易”还是“俏丽”上?如果它能担保一定程度的“俏丽”,并不再难以制造,是否仍旧具有艺术代价?本日的天下不可能产生卡拉瓦乔(编者注:Caravaggio,意大利画家,巴洛克画派代表人物),纵然有人能够创作出完备相同的艺术品,他们不会拥有卡拉瓦乔的作品在当时所拥有的代价。以是,我认为DALL·E的意义在于立即抛出这个问题:物体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物体有代价?为什么人类的艺术能力很主要?此时此刻的历史意义何在?这是一个有趣的征象。
再以ChatGPT为例。它的涌现让很多人开始担心人类的写作能力和拥有独立想法的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同样,它的浸染是让我们把稳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人工智能也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大概这些事情一开始就没有那么独特。我们可以通过算法创作电影剧本,那么我们该当问:既有剧本是否本身包含了太多套路才使得算法模拟如此随意马虎?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真正接管过ChatGPT,我乃至不想考试测验。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它有用,我也确信它对付一些事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我认为,一旦你放弃人的主动性,就会很舒畅地让其他实体代替你自己思考。
界面文化:选择与人工智能产品保持间隔,这会影响你对付人工智能的真实理解吗?
米勒:我不是社会科学家,我对评估人类对技能的反应不感兴趣。我认为理解不同的技能并及时理解新技能的发展非常主要,但说实话,我更感兴趣的是新技能如何与国家权力、大型科技公司和企业共谋,例如这些科技是如何被利用、被发卖和被动员的。
界面文化:人们一样平常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这一轮新技能之以是能够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由于它确有独特之处。它不再只是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纯挚是基于大数据的模拟和推演,而是彷佛蜕变出了某种“意识”。例如,《纽约时报》的一名科技专栏作家记录下了他与谈天机器人的对话过程,在对话的末端,谈天机器人乃至发起让这位作家离开他的妻子。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当下涌现了一些新的面向。它不仅仅是由一系列的数学规则组成,它知道人类不仅须要信息,还须要建议,乃至是情绪支持,被回应、被理解的须要。虽然它总体来说还比较低级,肯定不能完备取代人类,但彷佛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
米勒:我认为你刚刚提到的关于人工智能具有供应建媾和情绪支持的不雅观点是精确的。当这些程序变得更加繁芜时,它们当然将开始具备与人类感性联系的能力,对我们进行标准化情绪相应和情绪维度互动。但我不认为这令人工智能成为了有知觉实体。我们必须明白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它将不断引发诸如“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危险的,由于我们很随意马虎被愚弄。只是由于它展示了某种行为,我们就认定它有感知能力,这是不对的。
界面文化:你在自己的书中也花了许多篇幅来剖析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特殊是影视作品中呈现的亲密关系和性关系。从精神剖析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若何反响了人类对付人工智能的认知?
米勒:我利用电影媒介来研究人们是如何抱负人与技能的关系的。科幻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体,它戏剧性地展现了我们所面临的繁芜问题。目前许多技能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尚不存在,但当人们在《银翼杀手》《机器姬》《攻壳机动队》等电影中看到这些场景,多少会被迫思考这些非常繁芜的问题:当一种外表类似人类的高度繁芜的技能与另一个人类进入关系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电影中一次次看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的戏剧化呈现。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有趣的是,人类如何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想象人工智能是有感知的。我们想象人工智能有答案,想象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安慰的来源,这些希望显然勉励我们连续努力创造这些形式的智能。
我们须要清楚,虽然虚构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但它们是深度交织在一起的。回到你刚才举的例子,我们与人工智能谈天,人工智能转过分来对我们说,“哦,我认为你该当和你的妻子离婚。”这种人工智能的生理治疗用场,这种理解人类生理的系统化方法,很长一段韶光以来都是精神剖析历史的一部分,并且受到精神剖析本身的批评:仅仅由于某种算法可以方案得出你该当见告某人什么,或者该当根据他们的社会状况或特定的感情状态如何表现,并不虞味着有一种普遍适用的算法可以拿来就用。
以是,认为算法可以轻易地完备理解人类的想法,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由于生理治疗须要真正的人际关系,房间里的双方都受到自己的失落败、希望和繁芜性的影响。一旦个中一方不是人类,而是一台机器,无论这机器多么繁芜,我们也不知道它们的“建议”的终点是什么,“动机”又是什么。我们不可能轻易将人更换为人工智能,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而已,并不包含完全的故事。
03 人工智能家当的驱动力极其男性化,并与成本主义同构
界面文化:说到人机相恋,很多人都会想到电影《她》。它描述了一位离婚男子与拥有迷人声线的机器人相恋的故事。你的书中也有过关于《她》的精彩剖析。详细来说,精神剖析为理解《她》供应了哪些启示?
米勒:我关注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性(sexuality),特殊是在精神剖析术语中所谓的性化(sexuation)。性化指的是一个人在其主不雅观性中所处的位置,这将决定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付精神剖析来说,性别和性行为与措辞关系很大,与解剖学和生物学关系较小,我们感兴趣的是与措辞的关系如何决定我们的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在评论辩论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干系的原乐形式时,我们常常谈到构造,有诸如阴茎反应和女性侵害科学等观点,试图表达我们与措辞的某种联系办法。
我感兴趣思考阳具思维和女性思维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相互浸染,这一点在《她》中非常明显。比如你可以从某人的身体中抽象出某人的声音,这便是我们在《她》中看到的,这个抱负环绕着男主角华金·菲尼克斯与运用程序中完美的算法女友展开。人工智能由斯嘉丽·约翰逊配音,她是一位年轻俏丽的金发女子,她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电影制片人也知道我们知道斯嘉丽·约翰逊长什么样。而华金·菲尼克斯的角色是范例的、心怀不满的年轻单身汉,在成本主义中感到孤独和迷失落。他的办理方案便是在算法女友身上寻求能知足他所有需求的完美答案,这避免了繁芜的、完全的人类女人带来的混乱。从实质上讲,这种关系对他有用,知足了他所有的详细需求,以至于他必须找到一个化身,与她发生身体性行为。
电影结束时发生的反转非常有趣。这个算法女友变得如此繁芜,以至于她无法再与他互动,由于他作为一个人太大略了。我对此的理解是,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女性原乐超越了他,她能够以远远超出人类的速率与数百万人互动,由于人类太大略了。我很喜好这个想法,一个傲慢、狂妄自大的男人认为他可以通过算法办法捕获女性,并把她装在口袋里;末了情节反转,她变成了一种无限的聪慧,速率飞快,以至于无法再次被保留在一个人类男子的手中。
因此我喜好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非常女性化的原始力量,它有着向所有不同方向爆发的冲击力。然而人们一贯试图以非常男性化的、阳具性的、工具性的办法遵照某些规则,比如“我希望你作为一个女人去做这个和这个”,女性并不愿意如此,她们说:“不,我想做其他统统。”
从精神剖析的角度来看,这让我们回到了一种非常经典的模式——歇斯底里为女性主体,强制症为男性主体。在精神剖析中我们常说,歇斯底里的主体是真正的主不雅观性,由于她是一个不接管主宰者威信的女性主体,总是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要见告我我是什么,由于你不可能知道我是什么。”因此我认为,电影《她》非常好地探索了对男性统治希望和女性逃离男性统治的希望。
界面文化:如果从性别维度来不雅观察人工智能,女性主义的视角可以为我们供应若何的启示?
米勒:一旦我们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和构造的产物,就不丢脸出,人工智能能够实现的技能深受其产生的思维构造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目前主导人工智能家当的驱动力是极其男性化的,是和成本主义同构的。在这些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等,都是特定类型的人,有特定的兴趣。显然,这也影响着他们感兴趣的技能类型以及根据这些思维形式形成的同盟。
但这只是思考人工智能的一种办法,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还有很多未被探索的潜力和可能性。我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一部分缘故原由在于,我们开始想象人工智能的想法之前,就开始解析智能本身的观点。什么才是真正的智能?这个观点是如何涌现的?它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科学层面是如何发展的?这些变革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性别不雅观念、权力不雅观念和性不雅观念中。我们须要更加细致入微地理解这一点,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力。我并不反对人工智能,我反对的是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中的压迫、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紧密相连的办法。鉴于人工智能有如此巨大的潜力,我们须要把它看作与人类意识一样繁芜的领域。它有多么繁芜,我们就该多么重视关注它的潜力。
界面文化:还有什么是你想与我们的读者分享的吗?
米勒:我还想大略谈一谈加沙。目前人工智能的一大问题是它与工业战役机器的关系。实质上,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参与杀害大量人类的事情。在目前的加沙战役中,人工智能被作为一种极其恐怖的技能来利用,它与成本主义息息相关,也与那些乐于从战役中牟利的天下强国息息相关,后者对战役所带来的利益很有兴趣,但对其所摧毁的生命绝不在意。现在以色列正在利用被称为大规模暗杀工厂的“福音”(Habsora)人工智能系统,它在过去几周里杀去世了成千上万的人,大多是无辜平民。这些技能是真实存在的,且处于人工智能产生和传播的最前沿,权力精英在正在参与其生产。我们必须对此当心并武断反对。
(除注明外本文图片均来自豆瓣)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