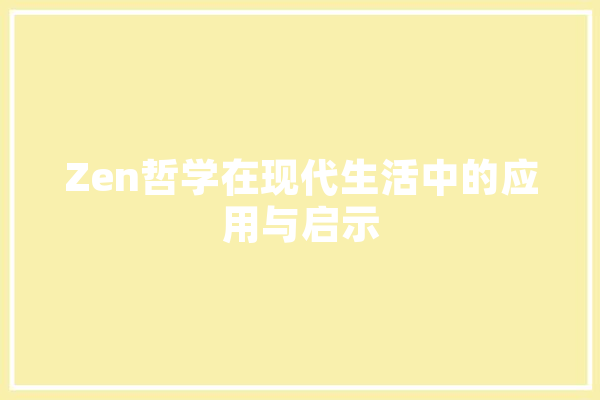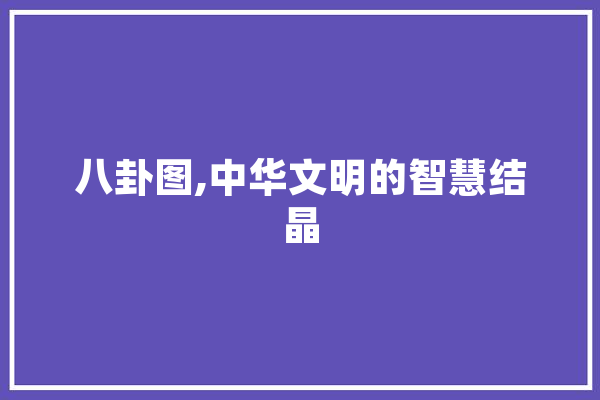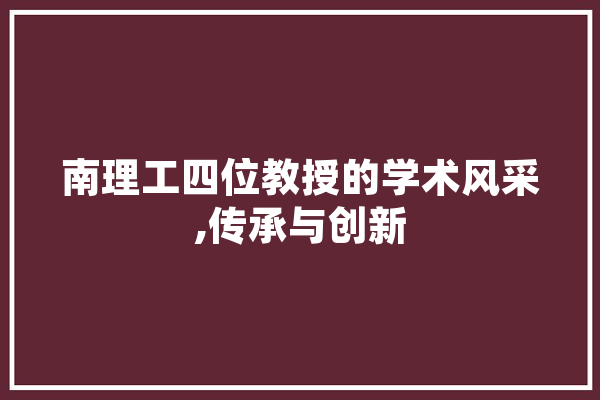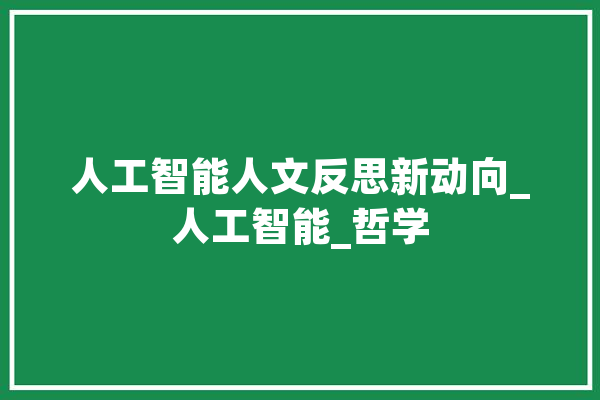何怀宏:躺平的时刻不妨读读哲学_传授_哲学
在何怀宏教授看来,当事态、心态涌现严重危险时,确实须要大声疾呼,开出猛药,而在不紧迫不严重时,温和、持久、武断的办法是最为有效的,“最好不是那么激烈,又不是不作为的放弃,逐步地濡染开来,我多年前接管采访时曾说,我乐意温和武断、中道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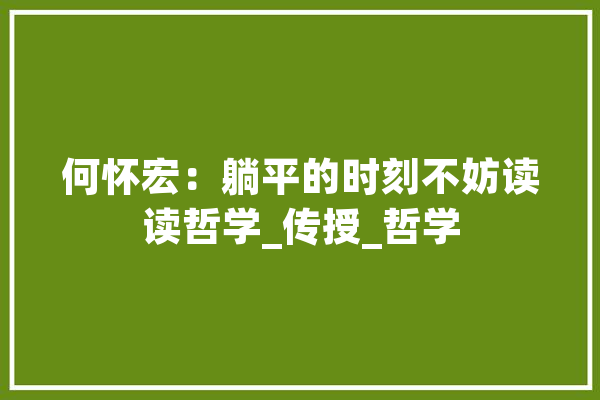
在这样的态度之下,何教授给“后浪”写下了《仅此生平——人生哲学八讲》,该书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想与年轻人谈谈朴素的人生哲学。何教授认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莫测的时期提前到来,天下不会再那么沉着,心灵也不会那么沉着了。他想见告年轻人:“天下将不会回到过去了,但生活和立身的一些基本准则可能还大致类似,我们大概还可以希望有另一种‘未见之事’,就如我读到的一句话,‘信便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的得到者,西方哲学经典的引介者,被季羡林称为“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精良学者”。主要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生生大德》、《新纲常》、《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转型中国的社会伦理》(英文)等。另有哲学随笔和文集《若有所思》《心怀生命》《比天空更广阔的》《中国的忧伤》《独立知识分子》等。编有《西方公民不平服的传统》《生态伦理》《平等二十讲》《域外文化读本》等。译著紧张有《正义论》(合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沉思录》、《道德箴言录》、《伦理学体系》(合译)等。
写给后浪的人生哲学课
2015年,何怀宏教授出版了写给孩子们的增订版《心怀生命》,写作初衷是他认为谈成功的书够多的了,谈生命的书还很少,而“珍惜生命的知识最好从小就融到孩子的生命中去,作为生平的根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命和比较康健的发展,成功和幸福都是随后的事情。
《仅此生平——人生哲学八讲》完成于 2018年春天,何教授在书中呈现了八堂有温度的人生哲学课,送给那些茫然无措的年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人该当追求什么:财富?权力?名声?卓越?幸福?利己主义便是自爱吗?心灵与身体是若何的一种关系?你以为孤独、寂寞、生僻的时候,怎么去处理?人生苦短,境遇无常,有限的生命何以彰显真正的代价?……这些看似无用的问题大概不能帮你决定本日吃什么最有滋味,却对人生中的重大决策起到提要挈领的浸染。无论是家庭、学业、事情、爱情还是人际交往,哲学都可以给你启示。
何以《仅此生平》今年才出版,何教授阐明说,他起初担心就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浅了一些,对少年人的阅读兴趣和习气来说又深了一些,因而搁置了许久。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暴发之后,何教授以为还是有必要“拿出来”,由于这本书本意便是写给“后浪的”,“‘后浪’是前不久变得时髦的一个词,当‘前浪’消逝在沙滩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归大海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不论那一层浪能拍起多大的水花,产生什么样的景不雅观,海是一体的,水是同质的。以是还是拿出来吧。由于它毕竟本意便是想写给后面的年轻人的,或者笼统地说,是写给‘后浪’的。其余,它毕竟也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而不是一种艰深的玄学。我在写作时心中所悬的,并想与之对话的阅读工具并不是哲学学者。”
疫情的发生,令很多人的心态有了变革。何教授说自己日益有一种担心,且在最近这个特殊的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日益强烈,那便是对未来的担心,“预感未来的数十年,将是变革莫测的数十年,可能还是困难和充满寻衅的数十年”。
何教授在不久前出版的《人类还有未来吗》一书中,从底线伦理和中西传统文化聪慧的角度稽核了人工智能和基因技能与人类未来的关系,并提出了预防性的道德与法律规范设想。高科技的各类寻衅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何以为人,何以为物,人曾作甚,人将作甚?“纵然没有这场疫情,我感到忧虑的一些变革依然存在,比如我在《人类还有未来吗》中提到的,对付科技,对付文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由于疫情一些方面显露了,乃至激化了。”
也因此,何教授认为让年轻人多理解人生哲学,在当今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与其他同样会去世的动物比较,人最特殊和优胜的地方在于自我意识,人能故意识地操持自己的生平乃至追求某种永恒。何教授表示,人生哲学就可以说是一种“向去世而生”的自我意识和理论,便是对人生从一样平常的善好到至善的各类意义的探求。
“人生哲学便是对人生的系统思考,尤其是一种反省式的系统思考,大家都有‘人生不雅观’,即大家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意见,人生哲学却不一定大家都有,许多人没有系统和一样平常地思考人生,也不一定系统地思考过自己度过或将要度过的生平。人生哲学便是以人为中央,思考人活着的意义的哲学,思考人该当如何良好地生活,如何故意义地度过自己生平的哲学。”
历史和哲学可以淡化灾害对我们生理和个人的影响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令人谈之色变。不过何怀宏教授却说自己的心一贯很沉静,归结缘故原由,何教授认为是哲学让他看淡死活、灾害。“历史和哲学可以淡化灾害对我们生理和个人的影响,以是(疫情期间)我确实没有什么恐怖。”
疫情除了带来一些外在日常生活的不便,以及出国、旅行、线下互换的影响外,何教授表示自己的外在生活办法没有什么变革:“这期间我照常如旧,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自己的心态没什么变革,外界的变革在我预期之中,小的问题也只是带来不便,没有影响到生活的大局,以是也不是很在意。”
虽然心态没什么变革,但除了关心***外,何教授还重读了《鼠疫》、一些关于瘟疫的历史书以及当代作家、年夜夫写的有关疫情的书,“读了一些如果不是发生疫情的话,不一定会读的书,读这些是由于我想理解历史。”
何教授1954年底出生,他笑说自己也算是经历过一些事情,“有一定的阅历,我在大学之前在社会底层待过十多年,工农兵都做过,人生中也碰着过风险、挫折,乃至想过自尽;现在也过来了,生活得挺好的,如果那时熬不过去,就白白捐躯了。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以为什么都没那么恐怖了,但要有阅历,你就得活着啊。”
何教授说他对哲学发生兴趣是由于对人生有兴趣,“不只自己的人生,还有别人的人生”。另一个缘故原由,在那个图书匮乏的时期,哲学书相对耐看,一本书在手可以反复看,过了一段韶光再拿起来看,依旧有“看头”:“我最初看哲学书可以说正处于自己的人生低谷时,也不是故意地搜索哲学书,便是无意间碰到了,我与哲学确实有一种缘分。”
何怀宏最早看到的哲学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像马克思的从前著作,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条记等等。“那个时候谈不上独立的思考,但由此也对前面的德国古典哲学发生兴趣,比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从他们还可进入到哲学更为深广的海洋之中。最初的入门就像是打开了门禁,进去之后创造门后还有各种路径,是要靠近大河、池塘还是海洋,还有很多路径让你选择。”
在何教授的诸多译作中,以古罗马哲学家天子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最为出名。2007年,温家宝在新加坡访问时,不但引用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还说:“这本书每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每天都在读。”何教授说他也一贯持续地受此书影响,变得温和而武断也与此有关,“一方面不那么激烈,怕烧伤自己或者灼伤别人;另一方面又不是无作为地放弃,仍旧武断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后来无论是遭逢外在风波还是个人不幸,他都会翻翻这本书,“我总能从中读到一些让我沉静下来、连续努力的句子”。
仇必和而解,不要制造和引发恶意
何教授对自己的期望是肚量胸襟越来越宽广,“我希望自己的晚年变得像大海一样宽广,年轻时奔驰彭湃当仁不让,晚年快到入海口时,应是温和而武断的,可以激浊扬清,坚持生活原则但又不那么苛求,原谅地看待统统。就像是大海,如果不能原谅泥沙,哀求的都是清澈的水,那大海就不能称其为大海了,以是心胸要只管即便宽广。”
只管已经可以原谅地看待统统,但不代表没有态度,何教授直言,看到有的学生被一群同学霸凌的***就以为很悲哀。也因此在《仅此生平——人生哲学八讲》中,何教授专门写了一章“德行培养”,何教授认为,德行不仅是人生成功或顺遂的手段,本身也是人生目标。一个人纵然不堪利顺利,他也能够在自己的德行里安心自足。努力追求德行的人乃至就将德行的圆满具足作为自己最高乃至唯一的人生目标。成功须要许多外在的条件,而德行却不须要,在这方面人是大有可为的。德行培养的意义还在于,如果我们让它们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气,那么一些下作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做不出来。
何教授特意提到了诚信、同情、年夜胆、公道、容忍、自律,在他看来,这些不仅是学哲学所须要的德行培养,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教诲。霸凌同学的人显然是短缺同情心的,何教授认为对他人痛楚的同情或者说恻隐之心在道德上更为纯粹。“它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初始源头和动力。我们乃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忍之心的普遍存在,才使我们即便在一些阴郁的时期里也对人类抱有希望。”另一方面,何教授认为恻隐之心仅仅是一种道德初始情绪的涓涓细流,要成为恰当的道德行为,真正地帮到别人和有益社会,就常常还须要有道德理性的判断和辅导,须要有道德意志的加持和加强,否则,它也可能很快流失落,乃至走向缺点的方向,“只有当这些力量汇合到一起,让同情成为我们的一种稳定的德行,并结合其他的德行,它才能持久和明智地发挥浸染。”
何教授认为,哲学的一个救世意义便是淡化恶意,就像冯友兰晚年反复强调的“仇必和而解”。“世上没有绝对的年夜大好人坏人,我不明白怎么有人就像斗鸡一样,总是睁大眼睛去创造别人的弱点,创造恶和丑,总是开释恶意,说话攻击性太强,动不动就完备否定别人的人格,我对此比较忧虑。很多人不看事实,动辄就做道德判官,但你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人理解多少?怎么能通盘否定呢?网络发言是匿名的,以是很多人不看事实,总是不雅观点态度先导,一上来就势不两立誓不两立。”
何教授反对那种主动的开释恶意,也不主见“以恶制恶”,即以不正当的手段抗恶,由于这样恶就会蔓延开来,甚至不可整顿。“就像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瞩目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瞩目。”何教授表示,一个平等多元的社会固然好,人们可以在个中享受多元,但一个条件条件是:人们同时也要忍受多元。在多元的代价和生活办法中,有些可能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喜好的。这时我们可以想想:当别人容忍我们同样异类或少数的生活办法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应该容忍其他异类乃至多数的生活办法吗?我们可能还是说不上喜好,却必须原谅和容忍。如果这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气,一种德行的哀求,忍受的烦懑也就可能减少乃至不存了。
不仅权力要容忍权利,多数要容忍少数,每个人在得到别人容忍的同时也须要容忍他人,这是自由的条件或者说社会根本,容忍不仅是握有权力者特殊须要具备的德行,也是社会的每个成员须要具备的德行。否则,当弱势者得势,他们又可能反过来压迫新的弱者,压迫只是换了新的主体和工具。要冲破恶性循环就须要引入新的原则和德行。
何教授认为人性在所有世代和地方实在都是差不太多的,关键的是一个社会是更随意马虎鼓励善还是恶。人的本性华夏来就既有善端,也有恶端,人性并不是一块“无善无恶”的“白板”。源头善并不能解释和担保终点。说“人是游手好闲的动物”“人是利令智昏的动物”,这都是说恶端发展为现实的恶,与他们的分外境遇有关,以是,后天的努力和习染是主要的。一个好的社会便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氛围能够勾引人向善而非向恶的社会,一个好的个人也便是能够引出别人同样好的情绪与行为,而遏止别人坏的情绪与行为的个人。“总之,我们对人性要有基本的信赖和当心,不高估也不低估。但是准确地估计和平衡有时并不随意马虎,这样我们或容许以说,在一样平常个人尤其是自我方面,我们对自己与邻人向善的可能性与其估计过低,不如估计偏高。”
哲学让你既执着又坦然,既参与又超越
何教授坦承对付未来,自己是比较悲观的态度,但正由于一向悲观,也就不那么随意马虎失落望和绝望。他认为人掌握物质的能力,既是相互帮助的能力,也是相互侵害的能力,但这种控物能力目前是太强大了,变得有些恐怖了,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大灾害。
以是,何教授认为未来人类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抵牾便是人的自控能力和控物能力很不平衡,基因工程、超级智能等高科技使得人的控物能力在迅猛发展,也造成人相互侵害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道德规范的能力,精神提升的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又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强。“坦率地说,你很难把人的精神道德升华到天使的高度,但人如果又节制了天神的能力,将非常恐怖,而这个不平衡始终存在。技能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是双刃剑,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的侵害。”也因此,多看些哲学,让人性对自我的贪欲多一些掌握,让全体社会和制度向善而行,在何教授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何教授笑说哲学的好处很多,“学哲学的人,读的是最好的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他们的思想、著作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学了哲学有助于你养成合理的思想方法,不管是上学,还是事情,都可以用到,哲学的通用性很强。哲学让你既执着又坦然,既参与又超越,让你渴望追求美追求艺术,让你有正向的人生态度,多和有趣的人打仗,不搭理无趣的人。”
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压力很大,少了很多玩乐韶光,大了又面临更大的竞争,何教授同情的同时,也笑着建议,如果累了想“躺平”时,不妨看些哲学书。“找适宜自己情形的读物,多翻翻,大概某一点就会对你有触动,以为自己已经躺够了,也可以起来溜达溜达,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喜好的事情,那就更好了。”
文/本报 张嘉 供图/活字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