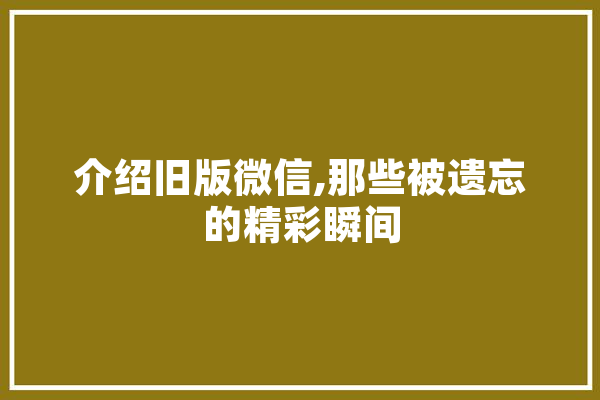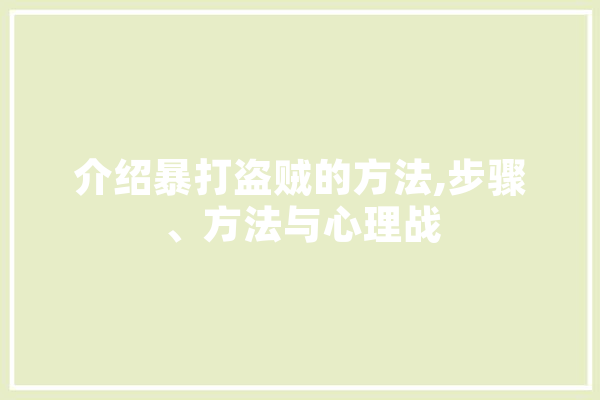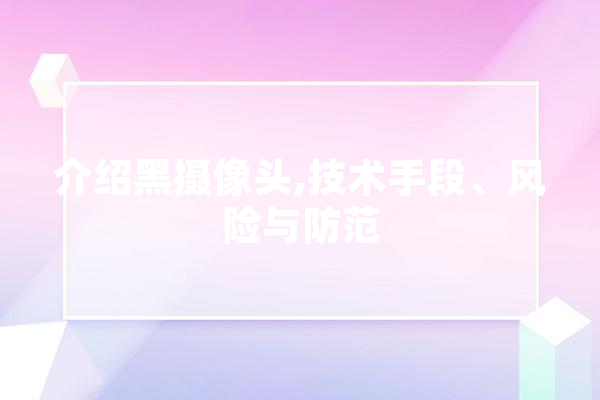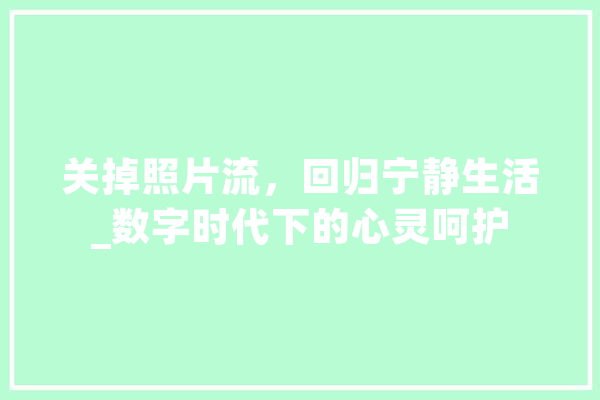邱华栋:AI的创造力来源_人工智能_人类
天生式AI最近又由于“可灵”鬼畜感十足的天生***火了一把:在各路段子手的调教下,容嬷嬷针扎紫薇变成了“午夜吃播”,刘华强火并瓜贩子也变成了激情亲切友好的街头联谊。如果说先前的AI换脸只是让人们开始疑惑身边的信息可能不再可靠,那么现在我们完备有情由担忧“真人”作者在未来的消散。然而,AI表现出的是真正的创造力吗?我们所追求的“创造力”究竟又是什么?今日推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布告处布告邱华栋的《AI的创造力来源》一文,让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时期并肩前行,寻回和创造生而为人的意义。 ——编者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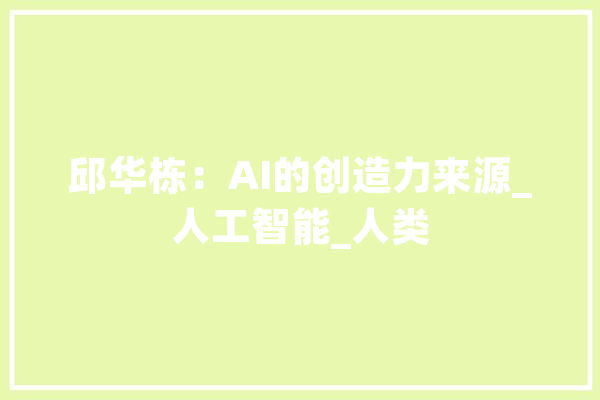
AI的创造力来源
——在2024中外阅读大会上关于
人工智能时期全民阅读的发言
今年春节期间,日本小说家九段理江利用ChatGPT协同创作的小说《东京共鸣塔》得到日本的芥川文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将AI视为其创作灵感来源,我们不知这句话是否言过实在,但大概我们见证了,一位以虚构为志业的作家公开表示,灵感这一超脱于规律之上的抽象特权已经被拱手让“人”,也由此须要我们展开思辨,谈论我们人类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与AI的关系,它能够通过什么参与创造力领域,继而考量在与AI同行的时期,人类的舞台是更广阔了,还是不得不与其分席而坐,划疆而治?
人工智能的探索路径和发展标准是为了让打算机像人一样产生思考过程。但现实是,人类至今无法单独依赖某一详细学科知识理解自己的聪慧,人文学者和作家更无法在灵感和天赋之外供应出可靠的关于创造力的阐明。我们也仅仅知道这个被天灵盖覆盖的大脑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本日,许多科学领域的论证彷佛开始愈发依赖神经科学家,比如对付大脑二性态的预测就须要由神经科学家进行揭示。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能可以证明,在详细情境下男女性别大脑的差异性反应(听说事实上差异的标准差极小),这些实验所能够供应的剖析,实在已经在各种层面深入到了过去由生理学、哲学等学科所主导阐释的领域。当然,脑科学大概能够不雅观察神经对美的反应,但依然无法独立理解美的呈现机制问题。可是,不妨碍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过去经由历史层积和审美浸润所确立出来的创造力的领地意识,大概正在产生真正的动摇——不仅是由于AI算法强大,而紧张是人类对自我探索的研究方法的范式性转化。
一
人工智能如今的运用已经非常广泛,早在1950年代,打算机科学家们就已经展开了关于这个新的技能方向和学科的问题。既然是一种技能,自然就会蔓延进入人的生活生产领域,文学艺术生产是人类元状态的精神生产,洞穴中的壁画、结绳记事的环扣都是在为人类用精准的措辞表达心灵天下做的漫长预热。因此,从很早开始,打算机技能就已经与措辞产生了勾连性的考试测验,比如机器翻译就有严格的语义对应,自动文摘系统能够提取出反响文章中央内容的短文,这可以看作是AI利用于笔墨创作的早期雏形,其特点便是被逻辑严格规定,***等实用文体写作也属于这一类,比如近年来的“快笔小新”、《今日》写稿机器人“张小明”等。以上这些紧张属于弱人工智能。
与之进行远间隔对应的是超强人工智能,在科幻文学中以各种瑰丽奇谲的面貌涌现。比如《2001太空漫游》的超级打算机HAL9000,它能够自主判断处境,争取自己的命运,乃至表演出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谋虑诡计。
《2001太空漫游》中的HAL9000
从现有发展水平上看,我们更须要谈论的是在现实和抱负之间处于过渡地带的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呈现”出与人近似的意识,与人类展开交互式学习。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创作实验上小荷初露的正是这一类人工智能。诗歌,这一措辞的黄金,承载着人类最光荣梦想的文学文体最早作为试验田而被开拓。早在1960年代,智能诗歌软件“Auto-beatnik”就已经“创造”出公开拓表的诗歌;1984年,梁建章以《唐诗三百首》《千家新诗注》为数据原本开拓出智能写作格律诗软件,在半分钟内即可根据哀求作出一首五言格律。此后不绝如缕地产生这一类似产物,最出名确当为机器人小冰《阳光失落了玻璃窗》(2017年),小冰本“冰”得到了在报刊上开设专栏成为专栏作者的殊荣,在诗歌领域造成轰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AI天生的诗歌措辞皆为外部措辞。
微软小冰的3D形象
AI能创作小说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小说逻辑与诗歌逻辑不一致。1966年,首个谈天打算机ELIZA出身,这为打算机日后开展虚构阐述能力供应了条件。在1990年代往后,打算机写出的小说越来越多。最具有戏剧性的事宜,一个是2017年算法程序 Mary Shelley重写了玛丽·雪莱的同名小说《弗兰肯斯坦》,而那部人类玛丽写于1818年的长篇小说被视为西方当代文学史上的首篇科幻小说;另一个便是,2018年陈楸帆的短篇小说《入迷状态》个中部分内容即是由人工智能机器完成的,并以微弱上风在评比中(AI参与了评比过程)领先于莫言作品,其本人常雅谑自称“打败莫言的男人”。
为什么将诗歌和小说区分开来呢?诗歌紧张依赖于人类已有的数据库,尤其是严格利用韵律平仄规则的古典律诗,比如,一个生活于唐朝孩童的蒙学是从《三字经》和对对子开始的,学习古体诗的资源相对而言是一个封闭体系。小说则不然,它须要交互信息的参与,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写作小说的人工智能的运作应配备成熟的对话机制(谈天界面);另一方面,大面积互联网的铺设给机器的学习能力插上了翅膀,虚构叙事类的文学创作能力取决于数据库的不断反哺。
因此小说的人工智能写作过程中,人的浸染还是相称大的。备受瞩目的小冰诗集《阳光失落了玻璃窗》的出版也是同样,并不表示人工智能的能力,其优化和挑选完备是人在运筹,专家系统从一万多首诗中选取139首收录入诗集。其余诗歌的理解也必须有读者的高度参与。诗歌字数较少,领悟又寄托于意象上,也便是说,诗歌除了吟咏的节奏、字词蕴含的韵味,其接管须要依赖读者的“脑补”,这是诗歌AI写作彷佛更加发达生动的缘故原由。
除了一定框架下的文学创作等功能之外,人工智能的数据剖析能力也能利用到文学研究方面,相对付以往强调的“细读”,这是一种带有间隔的“远读”,大大提升了研究的效率,比如对付《红楼梦》中的虚词进行数据统计剖析(有一些多义字需人工再度甄别),很可能查验得出前80回由同一个人完全写出,后40回中有一部分较为靠近前80回作者手笔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抖音、快手等短***平台的广泛运用,最为直截了当地拉近了普通民众——特指那些极少公开进行文学和艺术表达的人——与文化表达的间隔。但无论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本人,或者专业从业者都并不将其视为专业领域的闯入者。那么,今年春节期间openAI发布的sora则可能预示着对付影像***行业的颠覆。只须要供应足够明确的描述,sora就能够天生连续的60秒***,这再一次刷新了对付人类行为模拟的理解。机器学习总体而言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学习本便是人类创造者能力的外化,只不过经由海量的打算之后,行为模拟被极大加速催熟,但间隔真正的质变有多远我们还下不了定论。
从以上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与文学领域的交叉实践可知,文学已经具备发生变革的势能,只是积极推动实践的人每每是具有科研属性的职员,而很少有真正的专业作家和非专业写作者。文学由于其较为分外的属性,并不直接带来迅速的爽感反馈,因此写作小程序或者APP很难涌现高度遍及情形。而且,文学创为难刁难于基本框架设计,对付语感声口等独特性的期待,对付逻辑和阐述节奏把控的哀求,都必须由更专业的写作者才可能产出合格的作品。目前我认为较为适宜人工智能写作的一种是网络小说,由于网络小说一样平常而言体量大、细节密度高,AI能够替人承担一部分的劳动。
影视剧剧本写作也如此,尤其是商业剧本本身便是多人团体互助的产物,人工智能能够补足多人协作时每每笔调不一致的麻烦。在科幻文学写作里人工智能的上风也非常明显,它强大的数据库资源和打算上风,能够如迷宫一样平常设置出较为繁芜弯曲的情节,比如科幻作家慕明就利用与AI共创的办法写作剧本。因此,在现有科技条件之下,人工智能的创作具有积极的面向,参与和赞助我们的社会文化生产。
二
人文学者近年来热议AI的焦点并不是效力,而在权力问题。如上文已经铺垫过的,文学这匹富丽完全的绸缎,是由于被注入了灵魂、灵感、心灵,才是绸缎泛出光晕的神来之笔。刘慈欣2003年写下的《诗云》,证明高档外星文明的恒星级算法亦无法冲破诗性关卡,大刘通过诗性这一抽象能力牢牢把握住了人类的肃静和权力。
广播剧《诗云》观点设计
不过,我们可能得承认,这样的举例反而人为地拉大了普通人类和天秀士物的鸿沟。机器算法即便冲不破那关键的无形之门,出身不了李白、李贺,但也并非绝对就创作不出贾岛经由苦吟考虑的诗句。而且,如果我们这么早就为灵感盖棺定论,认为它将永久不被提炼出可还原和可实证的规律,那么眼下人们写作的意义不就完备损失了吗?文学存在的意义难道仅仅是提示我们,人类已经有如此多的天才存在,而不是召唤江山代有秀士出吗。我想,灵感还是具有一定的谈论空间。
这就回到了那个我们文学学科谈论几十年的话题,作家能够被培养出来吗?以经典文学史看,作家险些都涌如今学院之外,尤其是中国分外的发展历史,作家来自于更为广泛的野外江湖地带。自从1990年代,许多学院出身的作家汇入到当代作家群之中,当然即便是从中文系取得学位的作家,我们也常日将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视为两张皮,虽然这两张皮分享了同一个缝制者,但总体而言依赖的是两块不同的大脑区域和技艺。近年来,社会出于对沟通能力的须要,以及学科自我开流的发展规律,创意写作确立为成二级学科,学院派要开始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创作须要什么能力,这种能力怎么传授?
首先是文学创作规律。乐不雅观一点说,写作演习是有用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成功学故事:一万小时定律,其最著名的代表达·芬奇便是从练习画一只只鸡蛋开始的。他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光芒下的鸡蛋素描的呆板重复中摸索到了抵达博识艺术境界的路子。规律学习紧张属于行为学习,但还有一种能力学习,譬如小学生能够通过影象学会数学公式,却并不一定代表他就能够理解数学,拥有数学思维。能够得到思维的聪慧,可能须要很多难以概括的揣摩,这一点难以揣摩的东西可能与学习者的自我,以及在言传身教中的经历有关。怎么能够达到数学思维和数学知识的领悟呢?举一个不太恰切的例子,正如佛教里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的关系,或者说是狮子和大象的关系。“理”与“智”,一个是取得觉悟的客不雅观条件,一个是主不雅观条件,依理而发智,有智方证理。再用意识和潜意识来论证,潜意识无法被勘破,除非我们都如周公旦和荣格一样,能以多种形式记录和剖析梦境。而且,潜意识并不是灵感的绝对来源,须要被意识故意识地从那个黑乎乎的洞口召唤出来。召唤行为是须要重复多次的长久努力。因此,写作当然也是可以教授的。机器的写作演习自然会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想象机器会不会遭遇“卡壳”问题,算力会是匀速发展的吗?就人类而言灵感的涌现每每都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果,当思维结束到一定的状态,现实生活以有时性给文学表达一些剧烈或者微弱的补充。在有时变革的行走路线中作品也实现了弧度变革。
说到打算程序,如果学院的培养也是按照时候表、知识构造、选拔目标严格规定的话,作者就很难有余裕进行思维的有效拓展。并且城市化进程和当代化发展使独一无二的故土逐渐消逝,大家都生活在同质性空间,作者原来精神底色的差异也彷佛在缩小。不过,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期来临,间接履历已经高度霸占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这确实在理论上许可,即便是同样知识构造和教诲背景的人走上各具特色的写作之路,比如科幻文学就很具有代表性。但在较为传统的写作题材方面,作家能够通过间接履历的加持而取得的文学认知性和审美性的打破依然是有限的。
在科抱负象里,人去世之前将意识先行上传,这个意识就变成了一种还能连续成长的客不雅观存在,比如一个爷爷在去世去的时候是70岁,但10年后,爷爷的意识并不会还在70岁的环境里打转而与子女们无法互换,相称于这份意识依然在被现实投喂。机器也一样,除非上载新的程序,如果没有新的补充,比如行万里路,广结心腹这样的壮游经历,一个最前辈的AI即便投喂给他最全的李白诗文全集数据库(李白自己愿不愿意,还是一个有待办理的伦理与法律问题),那么AI版李白也只是一个已逝的李白,我们期待的文学不是去世去人的文学,而是彷佛山谷依然能够传来其文学反应,期待的是那一瞬间灵魂交互的心驰憧憬。
不过,我们也不能对自己在数据库中遨游的能力太过自傲。人类仅仅是看似面临无边的信息洋流,却并无法想象出自己没有经历之物。信息茧房的冲破不是仅依赖网络信息的能力,而是磨练构建问题的能力,构建问题的能力是综合能力。以是AI还是得办理阐述搭建之外的困境,它怎么打破我们人类神秘的美学机制,进行审美累积?
文学生产过程中存在审美体验。AI的文学像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即兴演出,它的写作是“事先张扬”的(机器写作混在人类作品中参与评比本色上也是一场秀),在场不雅观众们等待的是这场演出的结果。但传统的作家写作姿态有事后总结的性子,并必不可少的附带有被授予魅性的过程。机器写作带来的是惊奇感、新鲜感、震荡感,但读者的感情共鸣每每被绝不惜惜地给到了具有不同写作姿态的人类作家身上,比如复兴古文的韩愈、官场苦旅的苏东坡、深奥深厚博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终极汇入的不仅是文学史,更是心灵史,通达统统有人存在的领域。这些伟大的先行者的存在,令后来者也不由生出敬畏,但却并不妨碍着他们拎起自己的长矛刺向风车。必须承认,历史拥有霸权,文学史也当然以相对稳定的代价不雅观携带着一定的遮蔽性,不过人们汲汲于证明自己拥有某种不朽特质的时候反而在局限性中塑造出独特美感。
机器写作终极的结果是一种汇编,我们指认不出3.0比2.0在思想和经历上有了那些差异。因此,我的一个判断是,只要有历史、有韶光的存在,人就永久停滞不了对自身的追问。这才是为什么文学、艺术一定有“经典化”过程。但人工智能的文学艺术不会有,由于旧的作品由于数据库更小和匆匆使突变发生的有时性相对更低,而势必被更新的作品淘汰。那么,这种文学通向的是新,而不是好。文学的实质和文学为何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那便是如果把创造主动权交给AI,解释人类根本不须要“创造”这件事,也不须要自己本身的存在。这倒并不是在巩固人文主义的成果和人类中央主义的自恋,除非我们真的已经来到了韶光闭幕的尽头,不然,和人有关的统统事情还是最大的意义。
三
当叶文洁说“我点燃了火,却掌握不了它”的时候,我们将火理解为一种变幻莫测的人造物。细细想来,叶文洁无法掌握的紧张是ETO组织的成员各自心怀态度,也无法揣测三体人对付地球是改动、拯救还是毁灭的意图。大概人类心智的实质便是火,一种一经点燃就不再易于受控的物质。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还是伽利略的太空望远镜,或者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或者约翰·冯·诺依曼的EDVAC方案,都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一步步脱去茹毛饮血的命运改造方案。在节制了工具、乃至于工具的工具之后,人彷佛进化为了一种新的物种。如果说一根钻木的棍子、一堆柴草,是最早可被划归为工具的物质,那么是火带来了最早实现工具递归的启迪,木棍作为人的胳膊的延伸,火则成为人类智能的跃迁,实现了从工具到心智的贯串衔接。
冯·诺依曼
在人类对宇宙公理的认知真正被一场危急倒逼展开之前,叶文洁实在已经把地球命运的哲学思考完成了。她进行的大量代价判断,暂不论全面与否,至少代表着理解力本身,因此,三体人既是叶文洁的目标,同时又是她的工具。技能不是客不雅观中立之物,它是不雅观念的产物,且同时在不雅观念之中。技能代表着人与他者关系的机制。
在人工智能写作中,生产主体并没有发生从人到机器的转变,而是人重新考试测验理解工具,让工具更像人,而不是让人更像工具。sora发布后,B站up主“AI疯人院”迅速反应,发布出一条3分56秒的《西游记》***,展示出混沌初开、石猴出世等情节。创作者先利用ChatGPT剖析原著,完身分镜方案,再利用AI绘图,继而利用文生***技能,因此在内容理解和***制作层面,作者有效理解了工具的递归性,是最关键的启动系统。当然,即便人失落去了对付创作结果的掌握,但人依然保有对付结果欣赏、评价、阐释、梳理和留存的权力。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是在其工具性的第一层级意义上被搭建和授予的。
但值得当心的是,天下不仅向AI供应数据,天下也在被AI天生的数据重塑。当代年轻人管社交网站上的许多***叫做“电子榨菜”,他们每每在吃外卖的时候选取一段时长得当的榨菜来“下饭”,而且无论是***的不雅观看者还是制作者都承认这些***在心力本钱上较为低廉。未来,有了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参与,高速繁殖的艺术仿制品自然是越来越多,成为休闲活动的必要补充。我不认为大家在适应电子榨菜之后,会忘却还有鲜美的小烹和满汉全席。但担心由于榨菜数据的大量涌现,会拉平数据库的估算,并且逐渐在评价体系下将那些糜费功夫的大餐挤入角落。机器写作上亦如是,如果机器反过来连续学习自己输出的新一轮数据,如果这些平庸的数据来源足够大,大概会诱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意识去模拟机器的思考,终极放弃情绪态度和审美偏好上的独特性,在一张跑过的旧舆图上连续圈地,终极结局当然是越来越小的探索区域和越来越表浅的深度。
不过,可能我们都意识到了,这实在不是AI时期的分外问题,而一贯在文学内部发生着。AI写作只是无情地凸显了我们对这种问题的焦虑,只不过本日我们换了一支名为AI的折射望远镜去不雅观察而已。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文学知识系统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有许多共性也有许多差异。本日由于人工智能时期来临,文学知识系统迎来了新的反思契机。以考古学为例,这个学科确当下性在发掘古典性,既极度的古,又是极度的新。解剖学知识学习和碳14丈量等当代科学技能并没有消弭金石学的浸染,但却进一步拓展了考古的深刻代价,古人的图画字迹也同样授予自然科学以厚度。这提示我们,有通识支撑的学问每每更不受固有体系的限定。主不雅观学问和客不雅观知识并不在天平的两端远远不雅观望,而共同组成了对天下的阐明。即便文学创作来源于个体生命,但能够被接管且进入流利流传的通道,还是由于基于精神底层的集体无意识,且出于同一时空的人类对付现实判断和未来预设的准备,这是思想和文化形成公共性的条件。
在这个巨大的系统里,AI的算力本身也在个中。因此,我们当下更为急迫的任务不应该是呼唤文学如何,而是大学科和通识教诲的设置,对人的知识性理解和情绪大概会逐步凸显出独特代价。排他性的知识壁垒让人们无法整全看待。但我们本日对付AI的谈论必须是多学科、多角度的。这样,我们对付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勾引。担忧AI僭越对人类“特权”实在很迢遥和虚幻,更值得担忧的是,我们对付AI话题对创造力领域参与一味采纳单一的态度。
早在20多年前,深蓝电脑就已经展开了与人类的智力作战。从当年的万人围不雅观到当下下棋机器人元萝卜成为儿童小棋手的“陪练”和监考人,我们已经适应了这个有人工智能相伴相生的天下。在现实的地皮上回望200多年前的“土耳其人”傀儡骗局,我倒认为个中不无意味,大概正是人们对付传奇的神往,在吸引着人类塑造出可堪传奇的事物。想象一下,土耳其人骗局席卷全天下,始作俑者肯佩伦势成骑虎,他可能会无数次充满惊惧地回忆起那个方案骗局灵光一动的瞬间。一块块木板和无数的齿轮皆为障眼法,藏在木箱里的真人棋手和行棋傀儡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似真似幻的邪术。这种能力根本不在算法之内,而是出于人的虚荣和疯癫。偏离科学和道德的判断,肯佩伦大概对付机器技能和打算事理理解有限,但他对虚构有着极为有魄力的想象。乐不雅观一点说,是他的年夜言妄语给了今天下棋打算机的灵感。因此,人类才是新天下的创造者,而AI和我们同行,共同创造更新的天下。
本日我们在人工智能时期竟然还要回到人类朴素的阅读行为,去深挖阅读的代价,探索阅读的方法,是由于在大学科领悟的背景之下,对通识教诲的铺设,对终生阅读的倡导,都能培养对“人”的知识性理解。这是本日我们共聚于此的意义。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