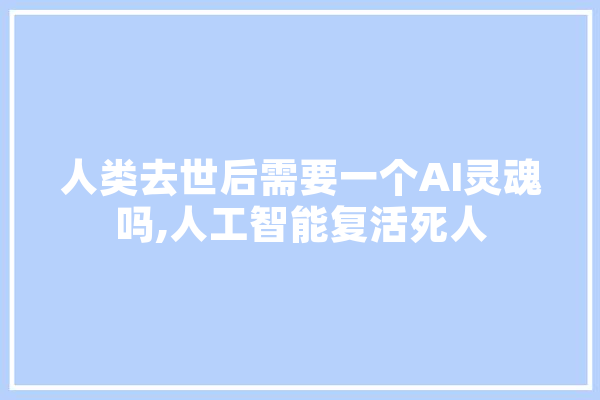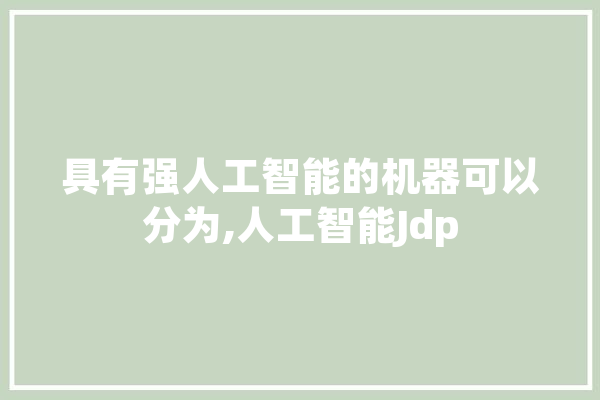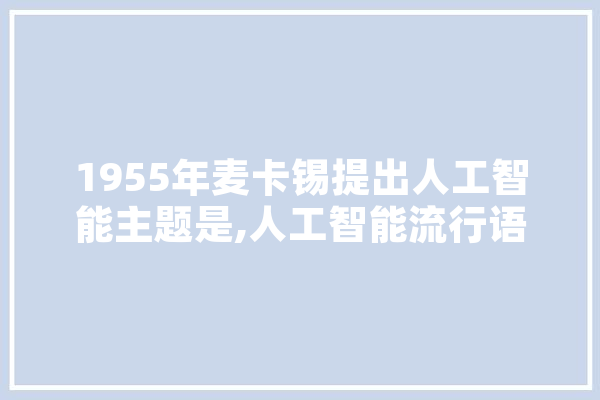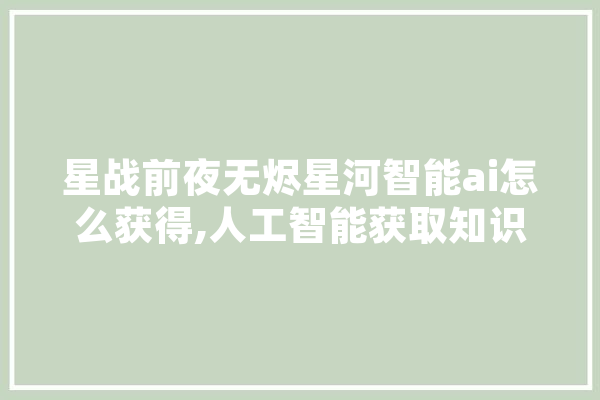顾真|戴斯蒙·麦卡锡:成就斐然的失落败者_麦卡锡_莱切
一

1919年1月,病痛初愈(“拔掉一颗牙齿,加之精疲力竭,犯了头疼,我卧床了两个星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决定每天晚上记录一点身边朋友的业绩,聊以自娱。她打算记下“他们的现状,描述几笔他们的性情,再评估他们的事情,预测他们未来的作品”。关于戴斯蒙·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她是这样写的:
要写戴斯蒙,困难在于你险些是要被迫去描写一个爱尔兰人。他若何错过火车,仿佛天生短缺航舵那样,只会随波逐流;他若何一贯在希望和操持,却踟蹰不定,靠伶牙俐齿一起通畅,编辑体谅他拖稿,店主体谅他赊账,还至少有一个贵族在遗嘱里留给了他一千镑……
伍尔夫说,麦卡锡懂得原谅,懂得欣赏,可能是他们这群人里性情最好的一个,但他“发觉玩乐太快乐,靠垫太优柔,闲混太诱惑,我有时候感到,他已经损失抱负”。文章结尾,伍尔夫想象这样一出场景:某天,她翻检着麦卡锡的书桌抽屉,在凌乱的吸墨纸和旧帐单中找出未完成的稿子,拿回去编成薄薄一本“桌边闲谈”(table talk),证明给年轻一代看:戴斯蒙是我们中最有天赋的。——“但他为什么一事无成?他们会问。”
戴斯蒙·麦卡锡当然没有一事无成。在伍尔夫写下这篇后的二十年里,他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最有大众影响力的评论家,也是伦敦文艺圈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先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当编辑,然后继戈斯(Edmund Gosse)出任《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首席评论家。他在富豪朋友布雷特(Olive Brett,Lord Esher)的帮助下创办月刊《人生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刊载了罗素、阿道司·赫胥黎、马克斯·比尔博姆等一众名家的文章。更是身兼数职,为好几家媒体供稿,为海涅曼出版社审稿,为BBC定期录制节目,风光无限。他交际很多,日程很满,派对女主人都喜好他、欢迎他,有他在,谈天就不会冷场;他的从容,他的儒雅,让所有人感到舒适。哪怕爽约,约请者也会体谅他。听说他会同时答应梅费尔(Mayfair)、布卢姆斯伯里和切尔西的三场饭局,末了不管现身哪一处,那边都为他保留了位子。从艺术家到政客,从运动员到学者,他都能交上朋友,哪怕是不雅观念、崇奉方枘圆凿的两个人,也可以同时视他为深交。麦卡锡曾说,从十七岁到五十岁,每一年他都能收成一位石友。
戴斯蒙·麦卡锡主编的《人生与文学》
白天精力兴旺的他夜里却常常失落眠,崇高的文坛地位并不能肃清他的愧怍。那是一种永久在冒死赶路却总也赶不上的愧怍。他赶不上坐车,赶不上赴宴,赶不上交稿,最要命的是,赶不上写他想写的书。多年来,他相信自己能写出比肩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精品,而且由于时常把年夜志和灵感表达得天花乱坠,他的朋友比他更相信这一点。1931年,五十三岁的麦卡锡出版了《画像》初辑(Portraits I),自序剑走偏锋,是一封写给二十二岁自己的信。“我把这本书献给你,年轻人,不过你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你会狐疑我是在嘲笑你,我承认,我是有点不怀美意。”麦卡锡坦言,青年时期心比天高,可三十载春秋过去,付梓的只是区区评论集,完备不符合当年的自我期许。他说,这封信不仅写给1900年的自己,也写给所有梦想当文学家却不得不靠给报刊撰稿糊口的年轻人。撰稿人的职业固然不错,但危害也不小,由于“思想的果实尚未成熟,就要采摘来招待客人”(must ever be cutting his thoughts in the green and serving them up unripe)。他向曾经的自己道歉:“我让你失落望了。”
戴斯蒙·麦卡锡
二
戴斯蒙·麦卡锡1877年5月20日生于普利茅斯(Plymouth),父亲是英国中心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高等职员,母亲出身世家,是一位脾气古怪的普鲁士贵族奥托(Otto de la Chevallerie)的女儿。麦卡锡资质聪颖,作为家中独子,从小受到父母倾力培养。他先后就读于斯通豪斯学校(Stonehouse)和伊顿公学,十七岁考上剑桥,入学三一学院,遵父命随名师学习历史。在剑桥,性情爽朗又善于体育的他非常生动,结交了许多终生好友。他剑桥时期最主要的一个事宜是加入秘密社团“使徒会”(Apostles)。“使徒会”资格门槛很高,须经由长期稽核,确保人品足堪相信,成员在离校三年后自动引退,“羽化仙游”(become “an angel”),但依然可以参加内部聚会。他在“使徒会”的活动上认识了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还通过弗吉尼亚的兄长托比·斯蒂芬(Thoby Stephen)与斯蒂芬家族结缘。“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初具雏形。与麦卡锡关系最亲密的是哲学家摩尔(G. E. Moore),摩尔只比他大三岁,却是年轻“使徒”们的精神领袖。多年往后,伦纳德对此依然津津乐道:
这是我常常乐于回顾的一幅画面:戴斯蒙站在火炉旁,用他温顺的声音讲述着一个离奇的长篇故事,而摩尔或是靠在沙发上,或是陷在扶手椅里,烟斗常日已经熄了,在一阵止不住的大笑中从头到脚都在抖动。
G. E. 摩尔
后来供职《新政治家》时,麦卡锡给自己起了个广为人知的笔名,“慈祥的鹰”(Affable Hawk),自嘲不修边幅的外表,也寓意追求以友善的目光洞明世事的境界。不过,青年麦卡锡差不多是其余一番面貌。1903年,伦纳德·伍尔夫初次见他,麦卡锡二十六岁,刚结束一轮老派的“壮游”(Grand Tour)返国,逸兴遄飞,英气逼人,无论说什么都能让听者如痴如醉,“他看起来像一只极为雄浑的小鹰,只要挥一下翅膀,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好心的仙子年夜方赐予了他每一种可能的天赋,尤其是每一个想要当作家或者小说家的人渴望的天赋”,在伦纳德和许多同辈友好眼里,那时的麦卡锡把全体天下都踩在脚下。
1906年,麦卡锡加入《自由党发言人》(The Liberal Speaker),撰写剧评,热心推介萧伯纳作品。四年后,他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结伴游览巴黎,拜访古董商和收藏家,回到伦敦在格拉夫顿美术馆(Grafton Galleries)策划了“马奈与后期印象派”(Manet and the Post-Impressionists)画展,马奈、塞尚、高更、毕加索等的画作让英国人大感震荡,一时恶评如潮。听说《逐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艺术评论家菲利普斯(Claude Phillips)走出美术馆的时候,把目录扔在门口,狠狠踩了几脚上去。除了广泛的人缘和残酷的口才,麦卡锡给身边朋友留下的另一大印象是混乱的韶光管理。与他伊顿公学式的温文尔雅相伴的是慵
《一些人,一些事》
三
《散文工厂:1918年以来的英格兰文学生活》
D. J. 泰勒在《散文工厂:1918年以来的英格兰文学生活》(The Prose Factory:Literary Life in England Since 1918)中试图磋商过去百年间影响文学家当的各种成分和这些成分塑造我们文学意见意义的办法,论及“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章节给了戴斯蒙·麦卡锡不少篇幅。泰勒说,青年麦卡锡之天赋异禀、出息无量,这险些是布卢姆斯伯里成员的共识。可他太热衷社交了(a social animal),总也沉不下心来写作,妻子莫莉(Molly)哑忍多时,急得向朋友抱怨道:“戴斯蒙没救了,他就像只小狗,门一开就往外蹿。”为了逼他创作,莫莉组织布卢姆斯伯里的朋侪建立“回顾录俱乐部”(the Memoir Club),会员不定期聚会,朗读新写的回顾录片段。可这番努力还是败给了他优雅的延宕。年复一年,麦卡锡为何写不出真正主要的作品成了布卢姆斯伯里圈内一大未解之谜(one of the great Bloomsbury Puzzles)。
回顾录俱乐部
作为麦卡锡亲近的朋友,伦纳德·伍尔夫在五卷本回顾录卷三《重新开始》(Beginning Again)中,对他何以没有兑现年少时的潜力做了详细的剖析,入理入情,值得一读。伦纳德认为,如果你立志写出一流作品,就不要指望白天靠给报纸供稿或者去出版社上班养活自己,晚上再负责写作,“哪怕当一个厨子、当一个园丁也比写一堆二流东西或者摆弄书本强”。当所谓的撰稿人,对年轻作家是陷阱,是幻象,由于写出的稿子不管是否署名,作者都会莫名其妙躲避掉某些任务。其余,麦卡锡的“拖延症”切实其实病入膏肓:
当他以为自己该当做某件事了,不管那件事是什么事,他急速会感到完备无能为力,然后去做别的事,不管什么事都行,来避免做那件该当做的事。那件该当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并不主要;乃至可能是他实在想去做的事,但如果那件事同时是他意识到自己该当做的事,他会不由自主去做他并不想做的另一件事,只为不让自己去做那件他该当做也想去做的事。
伦纳德·伍尔夫自传卷三《重新开始》
以是一旦麦卡锡发愿写他神往写出的小说,写小说随即变成了分内的辛劳劳动,到头来他每每会乞助于给报刊写稿来避免这种苦劳:报刊文章是他躲避写作严明小说的避难所。麦卡锡有聪慧、懂诙谐,想象力丰沛,措辞天赋高超,可以精准描述一个人物、一幅景象、一次冲突,这些都是一流作家的必备本色。但仅有写作的能力还不足。敢于出版自己投入巨大心血的作品,交付众人批驳,须要对自己狠下心肠。伦纳德说,一个作家在出书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书和我这个人;我要出版它,让别人见鬼去吧!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about it and me; I shall publish it and be damned to them.)作家必须为自己写的东西卖力,必须在公众年夜众面前充满美感地脱下衣服,跳进纷繁见地的冰凉河水。可麦卡锡一动笔写小说,时时瞻前顾后,处处恐怕言不及义,眼看就要掉入自我疑惑的泥潭,只好赶紧捉住书评、剧评的救命稻草,给《星期日泰晤士报》撰稿他可以放低标准,由于“他不是为千秋万世写作,而是为一个短暂的周末”(not writing sub specie aeternitas,but for a short weekend)。
戴斯蒙·麦卡锡
一战中,麦卡锡赴法国做事于红十字会,其间同毛姆建立深厚友情。当时的毛姆已是成功的剧作家,但尚未建立小说家的名声。他看到毛姆在改一份校样,好奇拿起来看,创造纸上改动极少。后来他知道,那是《人性的枷锁》!
他感叹,小说家毛姆和剧作家毛姆一样讲究实际(business-like)。对完美的渴求不会困挠他;差强人意就足够了(the adequate will do)。麦卡锡虽欣赏毛姆,认为他是叙事的高手,到底学不来这套不跟自己较劲的经济学。他熟读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史哲经典,从前推崇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后来拜服托尔斯泰,恨不得自己的作品凝萃古今精品之所长,同时避开其所短。希腊人说,最好是很好的仇敌。(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麦卡锡过度执着于写出最好的小说,结果反为所累,被字网困住了手脚,连很好乃至尚可的小说都写不出来了。
四
《聪慧的心:戴斯蒙与莫莉·麦卡锡传》
麦卡锡夫妇晚年的一大欣慰是觅得塞西尔(Lord David Cecil)这位女婿快婿,盛赞他是人间天使,“不仅有聪慧的头脑,更有聪慧的心灵,这比聪慧的头脑还要难得”(has a clever heart as well a clever head,which is rarer than a clever head)。许多年后,塞西尔的儿子儿媳为外公外婆立传,化用这句话做书名,再贴切不过,由于戴斯蒙·麦卡锡同样拥有“聪慧的心灵”。这让他在与人、与笔墨打交道时永葆理解之同情。比起思想不雅观念和自然风景,他对翻覆莫测的人性更感兴趣。他的不雅观点既符合知识,又富于想象力,他的文风优雅而晓畅,从不故作博识,善于见微知著,借助意象建立共情,他的目标读者从来是“有教化的大众”(cultivated general),而非困守书城的学究。麦卡锡欣赏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的文笔,说清爽的作家好比清澈的泉水,看似缺少深度,实则不然;深不可测每每是浑浊造成的假象(the turbid look most profound)。麦卡锡读书驳杂,诗文警句信笔掷出,俨然前两天从名流的家宴上新鲜听来。作为编辑,他的用稿宗旨从来是不雅观点有趣、笔墨好看。他说过:通往文化的第一步是学会感想熏染文学带给你的快乐。
报刊文章天生短命,再精良的作者也只能得到现世的关注,文学史永久是小说家、墨客和剧作家的主场。中年往后,麦卡锡逐渐接管了现实。他不复当年写出不朽之作的壮志,并且心怀戴德,说虽然当批评家不是本意,但既然一欠妥心走到了这一步(I slipped into it),在文学评论里挥洒才情,通报热爱,也很好。他对斯夸尔(Jack Squire)说:“我们是造诣斐然的失落败者。”(We are admirably successful failures.)在那封信末了,他与二十二岁的自己和解了,说要不是自己的
除了一册先容宫廷剧院(Court Theatre)的小书,麦卡锡所有的作品都是报刊文章,他曾对斯特莱切说:“我得每星期赶三篇稿子,直到去世去的那天。”1920到1928年间,“慈祥的鹰”的专栏险些每周更新,以慵
戴斯蒙·麦卡锡作品《画像》(1955年新版,去掉了1931年初版的“初辑”字样)
戴斯蒙·麦卡锡作品《回顾》
麦卡锡年轻时身体健硕,老来却频受哮喘折磨。伦纳德在自传里回顾了他与麦卡锡的末了一次相见,暮景残光,令人倍加感伤。麦卡锡去世前不久的一个秋夜,十一点钟光景,伦纳德和他刚参加完一次“回顾录俱乐部”的聚会,走到街上。景象很冷,麦卡锡喘得很厉害,伦纳德扶他上车,目送他拜别。在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的街角,他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和麦卡锡在德文郡的山间溜达,同摩尔和斯特莱切一起参加复活节的读书会,“目睹朋友老病牵缠的苦难,猛然忆起他们年富力强的景象,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难过了”。伦纳德戏言自己从未终年夜,或者说从未年轻过,以是永久怀旧,恍惚间难辨今昔,在自传的不止一处,感慨“闭眼青春年少,睁眼垂垂年迈”。
利顿·斯特莱切
昔日学生莫蒂默尔(Raymond Mortimer)笑言,麦卡锡爱阅读赛过爱写作,爱谈天又赛过爱阅读。不止一位朋友说过,戴斯蒙是他打仗过的最会谈天的人。伍尔夫夫妇曾经找伦纳德的秘书格林小姐偷偷速记他的言谈,这份记录如今不存,可据她讲,麦卡锡滔滔不绝,记下来却并不精彩。格林小姐的判断已无对证,但即便我们本日能看到那份记录,也未必会以为多么惊艳。笔墨可以传达说话的详细内容,却绝难传达说话者的风神。还是伦纳德·伍尔夫的话:麦卡锡活生生的本人(the living person),他的声音语调,他句子迁移转变的地方,他宽容、和蔼的笑颜,他皱起的额头,他透着诙谐闪光的敏锐眼神,一起造就了他的魅力。他不在了,这绝版的统统也随之云散。一个作者,如果本人远比作品有趣,被遗忘大概便是宿命。
伍尔夫夫妇
1952年6月,他回母校领受名誉学位时因哮喘引发的支气管肺炎去世。如今他安眠在剑桥,与至交摩尔毗邻而居。可惜,后人究竟没机会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想象的那样去他抽屉里翻拾片玉碎金了。在拜格诺(Enid Bagnold)的《自传》(Autobiography)里翻到下面这段,写她跟晚年的麦卡锡通电话:
在我中年(他晚年)的一天早上,他打电话来伦敦找我。
“我清理了我的书桌,所有东西统统扔了。”
“都有些什么东西?”
“几个第一幕。几个第二幕。如果一部剧没写完,维尔吉利亚,那就即是没开始写。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真是个悲哀的清晨啊。我坐着心想,”他标志性地轻轻一笑,“我写得多棒!
”
伊妮德·拜格诺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