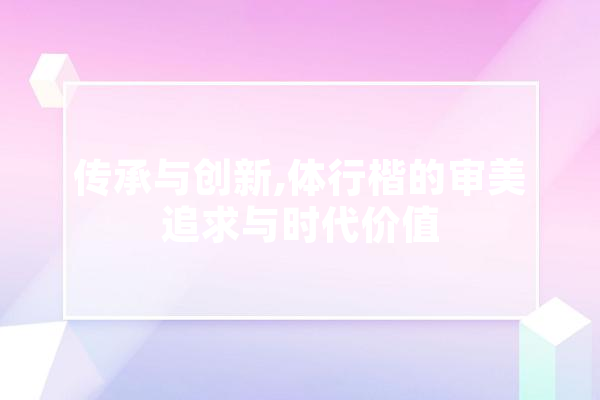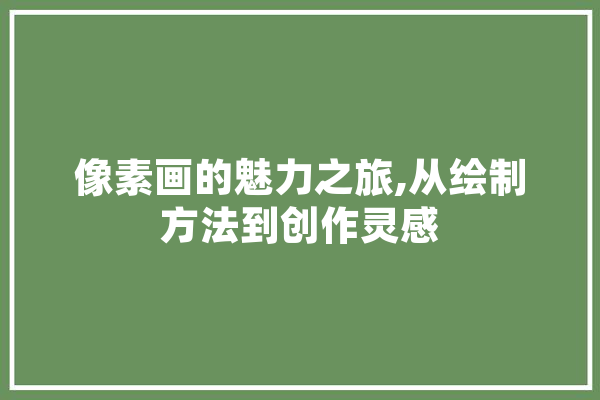同济“艺术与人工智能”论坛:立异之后该艺术发挥浸染了_人工智能_艺术
什么是人工智能艺术?机器是否也可以是艺术家?近日,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举办“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通过艺术、设计、打算机科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前沿学者和创作者的谈论,试图在艺术、科技、伦理的交汇处,共同磋商和构建当代人工智能艺术领域的知识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艺术领域目前最受关注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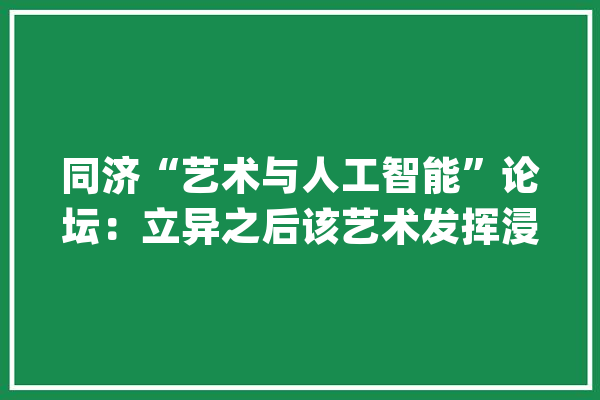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宣告正式成立,同济大学副校长兼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说:“艺术”的代价在于启蒙,而“设计”的代价在于改变,“过去同济把设计和创新绑在一起,但在这个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技能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时期,我们在用设计改变这个天下前,前所未有地须要新思考、新创造、新启蒙,全体天下须要再一次被唤醒。这时候,又是艺术发挥浸染的时候。”
2018年,法国的艺术家小组Obvious利用人工智能技能创作的肖像画《Edmond Belamy》在纽约佳士得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标志着人工智能艺术进入了天下拍卖舞台。此后,他们网络了超过5万张干系的日本版画的图像,基于这些数据库进行再创造,以当代的办法演绎传统的艺术形式。类似的创作形式还在延续。Obvious与来自非洲一些雕刻事情室互助,用人工智能天生面具脸谱,由雕刻事情室制作出真正的面具。目前,Obvious的作品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展出,例如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加拿大马蒂斯博物馆,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未来,除了艺术作品之外,他们希望将人工智能用于更广泛的创意领域。
法国艺术团体Obvious正动手利用人工智能技能创作的艺术项目
如今,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艺术领域,与此同时,关于创造力的尽头、作品的版权、机器的自主性、人工智能在艺术中的边界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环绕这些问题,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举办“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就此进行磋商。在这次论坛上,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宣告正式成立,这是海内首个探索ai艺术领域的实验室,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菲利波·法布罗基尼(Filippo Fabrocini)、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康思达(Kostas Terzidis)以及独立设计师、数字艺术家、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张周捷共同发起。
aai论坛现场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领导者,菲利波·法布罗基尼(Filippo Fabrocini)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人工智能设计事理》课程,并担当“可持续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他指出,技能可以是理论性的,也可以是诗意的。任何一种科技既能够成为一个独裁者,也可以变成贤人般的存在。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进步,同时也可以成为“毒药”。他认为如今须要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它应该是卖力的、透明的、公正的人工智能,该当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定义的。我们希望更好地阐明什么才是人工智能,我对此的答案就像以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情可以变得更加地丰富。”
论坛现场,菲利波·法布罗基尼
约翰·凯奇作品《4分33秒》
菲利波·法布罗基尼以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4分33秒》、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艺术家此在”行为演出以及杜尚的《大玻璃》作品为例,指出了随机性在艺术创作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而在他看来,随机性的背后始终有人类行为的干预。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同样是对付这种随机性的探索。
作为数字艺术领域的代表,张周捷认为,数字艺术正在迎来黄金十年,数字艺术中很主要的一部分是用算法来创作作品,但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更加智能的算法来创作,这便是人工智能艺术,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从常规算法进入到智能算法。但是,在他看来,目前从数字艺术到人工智能艺术还存在两个樊篱。“一个是技能樊篱,一个是运用樊篱,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便是以此为目的,汇聚多位艺术家、科学家、理论专家一起来谈论,如何让更多的人打破技能樊篱,参与智能算法艺术,同时共同探索其理论和表现形式。”
张周捷利用算法设计的传感椅
在接管媒体采访时,张周捷先容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不同阶段的目标,首先是通过不同领域的共同磋商,确定人工智能艺术的边界,第二阶段是基于同济多学科的土壤,让艺术家与科学家等结对互助,“由于人工智能艺术须要技能、艺术、创意、家当的高度整合,须要对工具的深层次理解和调用。” 第三阶段则是产出和表现,根据他的不雅观察,目前全天下大多数的人工智能艺术作品勾留在视觉层面,但是艺术还有雕塑、装置,乃至行为艺术,实验室期望探索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未来,人工智能艺术或许会出身出一些非常冲动人的作品,大概机器比我们自己更理解自己,大概人工智能能够算出人所不能想象的东西。”张周捷说道,“机器本身是人所创造的‘母体’,如今这个母体又创造出了丰富的艺术形式。”
艺术家Sougwen Chung基于自己的画作来演习AI,终极形成“画笔的二重唱”
康思达(Kostas Terzidis)是天下算法设计专家,他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哲学层面,“人工智能更像是一个哲学本体论存在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的存在,我们是谁。”在他看来,无论技能如何发展,艺术的完备消亡是不可能的,没有艺术的天下是无法想象的。“艺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职业,由于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技能的涌现,由于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技能的涌现,这个职业本身有一天会消亡,会降级,会被机器取代。其余艺术作为一个领域,它实在是个古老的传统,是存在的模式,如果没有艺术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存在了。”
康思达(Kostas Terzidis)
在康思达看来,设计关于探求,须要探求被藏起来的东西,在无数的可能性中探求最优的那一种。而人工智能的设计便是这样:从统统当中提取最好的。他以造句为例,“要把八个单词变成一个句子,可以有一千六百多万中可能性,而个中肯定有一句话是最完美的。”为了找到这句话,他可以创造一个神经网络,从中找到最好的句子。回到艺术创作的发展,“一开始有了画家,然后有了用户,有了编码,有了神经网络,现在我们有了排列。现在的作者是工具的作者;人工智能不仅仅要利用人工智能,还要去制作人工智能,然后才能够制作艺术作品。”
娄永琪
为什么同济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实验室?为什么一个专注“设计”的学院会探索艺术与人工智能交叉的这样一个领域?
作为实验室成立的推动者,同济大学副校长兼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给出了答案:“艺术”的代价在于启蒙,而“设计”的代价在于改变。学院在2009成立之初把名字从“同济大学艺术设计系”改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新学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刻意地和艺术保持了间隔,是由于那时候启蒙已经完成,设计该当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还是一味地和艺术纠缠在一起,就犹如在试图唤醒一个装睡的人那样徒劳或是如无病呻吟般的矫情。同济把设计和创新绑在一起,便是为了从“驱动创新”中探求设计新的动能。“但本日,我们反过来重新拥抱艺术,是由于在这个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技能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时期,在这个扑朔的后疫情时期,我们在用设计改变这个天下前,前所未有地须要新思考、新创造、新启蒙,全体天下须要再一次被唤醒。这时候,又是艺术发挥浸染的时候。”娄永琪表示,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建立,吸引天下上更多的人一起开拓人工智能科学与技能、艺术、人文、哲学、商业多学科交叉的新设计边陲,“尤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连续实现人、人性和人文的代价和肃静。”
任务编辑:陆林汉
校正:施鋆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