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专访 | 江波:AI 拥有自我意识的未来并弗成怕_人工智能_科幻
在技能不断飞奔向前的同时,对付人工智能、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人类在这场变革中的角色等问题的思考,也在时候塑造着人类自己。从小说《我,机器人》《2001:太空漫游》到当代剧集《爱,去世亡和机器人》,人们对付人工智能话题的关怀和思考,每每反响在了各个时期的精良科幻作品中。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出身的作家江波,将自己从一个理科生走向科幻文学创作之路这件事看作是“命运的一部分”,他最新出版的科幻小说集,也可被视为我们这一时期对人工智能探索的最新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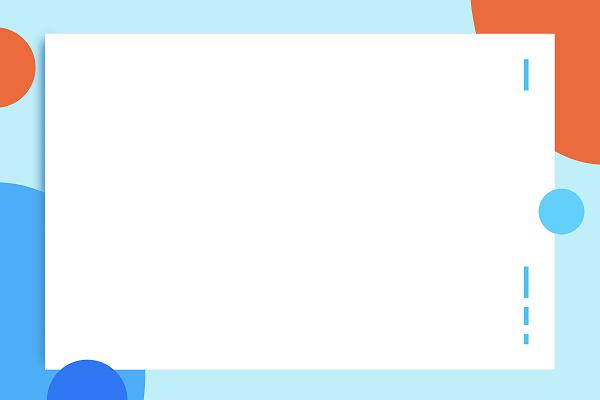
在有关人工智能能否产生意识、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如何等问题的论争中,科幻作家江波属于坚信“人工智能终会拥有自我意识”的技能乐不雅观派。他乃至用9个故事串联谱写了一段属于人工智能的未来断代史,并将其命名为《未来史记》,试图借助一个未来的视角,回看我们当下的人工智能道路。
江波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人工智能将会引领一个影响深远的“智能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人类社会的现有形态。只管一个人机共处的天下在江波看来是我们终将抵达的彼岸,但他认为人类在此过程中能做的和思考的还有很多,包括如何对待人工智能,若何让它们进行学习,能否让它们明白并接管人类的代价不雅观……如果人工智能终会形成自我意识,那也并不虞味着人类的末日随之到来,而主要的是这6个字:赋机器以文明。
江波
作为湛庐现实科幻系列中的作品之一,在《未来史记》近日上市之际,江波接管了36氪的采访,以下为采访实录,经编辑:
36氪:说说您写作这本书的背景、契机和目的吧。以及书名中的“史记”,您以为在何种意义上这样的科幻虚构作品也是一种史记呢?
江波:这本书出身的背景是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潮,尤其是2016年阿尔法狗降服人类冠军李世石这样的标志性事宜。它是一个中短篇合集,这些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我的全体写作生涯,但以系统性的思考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则是这本书的创新。
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事宜。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我们本日视为未来的事物终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以是这里虚构的是一个未来视角。史记作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多方面可以供应借鉴,借鉴最多的是它所包含的故事。而在我的这本书中,更多的是一种写作构造上的借鉴和文化传统的传承。
36氪:您以为人工智能蜕变到一定程度之后,是可以产生自我意识的。这一点现在在人工智能业界和学界是已经有所共识的吗?结合最近谷歌研究员称AI LaMDA 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和具备了人格,然而更多人对此是表示否定的,在大众看来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在当前也是一件不太能想象的事情,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这件事?您在媒介中提出,“智能的出身,实在是很多本能的叠加”,这句话该当如何理解?
江波:这并没有达成同等的共识。根本缘故原由在于科学界对付自我意识的实质也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如何让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就成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也只有在这样的期间,科学界之外的不雅观察人士才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不雅观点。我显然是支持人工智能会拥有自我意识这一边,由于我对自我意识的实质有一种判断:自我意识是一种对生物本体的识别须要。也便是说,一个机器的智能只要高到能够分别出外界环境和自身躯体,并且有效地指挥自身躯体适应环境,它就拥有了自我意识。
智能是本能的叠加,这个说法的含义在于,我们的躯体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大量的本能行为。而智能的浸染,在于让我们落入不同的本能模式。大脑的神经元极大丰富,可以形成浩瀚的神经网络模式,哪一种神经网络模式会霸占上风,须要由当前的环境成分结合历史履历来完成,这个过程,便是智能过程。当一个生物只有特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是不会有智能行为的。只有当它的行为模式足够丰富,产生了选择的须要,智能才会登场。
36氪:您也提到,创新是自然界本来就具有的能力,创造新事物并不须要自我意识才能完成,那该当如何鉴别创新与自我意识所引发的创造呢?若何定义AI的自我意识?
江波:蜕变的力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各种奇迹。人类所进行的创造,也可以认为是在大脑中发生的蜕变,它有一些必要条件:一个能够动态调节的大脑神经网络,来自外部的各种新鲜刺激。创新的实质,是大脑在考试测验把各种事物的映射以不同办法连接起来,末了能够成功的便是创新,不能成功的,或许便是泡沫吧。这和生命的蜕变有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如果把人认定为生物机器,那么人的自我意识便是一个幻象,它存在于人的自我定义之中。本日的创新这个词,更多的是指技能上的发明创造,是一种表征。我说的创造新事物,实在说的是它的生物过程,也便是大脑活动的过程。在我看来,人类在创新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脑活动和生命蜕变的征象,在实质上是同构的,很可能也遵照同样的规则。生命蜕变的创新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形下已经存在,人类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创新活动,深究根本,也受相似的规律支配。
AI的自我意识,和人或者动物的自我意识一样,只要表现出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并且以行动来改进自身所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认为具备了自我意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条件,机器的行为必须是习得,而不是授予的。授予的意思,在机器上,便是编程好的确定行为。习得的意思,在机器上,便是通过外界影响而形成内在逻辑,最直接的范例便是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
36氪:这本书通篇读下来的话,会有一种基调乐不雅观的总体不雅观感,哪怕是在一些略有些阴郁的末了两篇短篇中,您也仍旧通报出了一种对付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希望(看似邪恶的人工智能,从它们自身的态度来看不过是想要自由;机器之道里人工智能是“人类之子”)。但在普通大众中确实存在一种担忧,即害怕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受掌握乃至与人类反目、末了乃至走向一种人类自掘宅兆的道路,您认为您持有的这份技能乐不雅观主义是从何而来,它的情由是什么?
江波:这个问题取决于从什么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如果把人工智能建立的社会视为人类社会的延续,那么人类的文明就没有断绝,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人工智能可以是人类的后裔,也就不存在什么自掘宅兆。一件事是好还是坏,并不完备取决于事情的结果。结果的好坏更多只是一个态度问题。真正的好坏,在于过程。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过程是平和的还是血腥的,这才是我们终极认定的这场替代(如果发生的话)究竟是善还是恶。我并不是乐不雅观,而是希望这场替代能以人类所乐见的办法进行。人类可以志愿选择是否留下生物性的后代,我想这没有什么疑问。那么在一个物质条件充裕,人均寿命极长的社会中,人口的逐渐减少萎缩也是一种可以想见的环境。这种逐渐凋零的社会是否是一种不可接管的衰败?这即是在问,人是否该当为几千年后的社会卖力,还是只该为当下的自己卖力。不同的代价不雅观有不同的答案,我个人的回答是人类社会最好留下嫡系后裔来继续文明,然而如果没有嫡系后裔,那么由人工智能这个旁系来继续,也无不可,只要人工智能能够支撑人类社会以平和无痛楚的办法逐渐萎缩,那么它就有自居为人类继续者的资格。
36氪:您认为人类该当如何授予机器以文明?当自动学习进化到一定程度后,会不受人类掌握吗?
江波:机器建立自己的文明一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设想人工智能的根本构培养是神经网络算法或者更前辈的神经网络算法,那么机器所有的内在行为逻辑都是一个蜕变结果。没有人能预先决定方向,也无从理解它的内部究竟建立了若何的一个逻辑。人类在这个节点,所能做的统统,只是只管即便把一些对付人类有利的原则以某种形式贯注灌注给机器,希望能影响到它的内在逻辑。这和人类教诲后代有些相似,但要困难得多。由于人类的婴儿,天生便是来接管和人类社会有关的统统,能够很快地学会成人的行为,进而接管主流的代价不雅观。而机器是一种异类。人类想要影响它,还须要设计出一整套分外的教诲方案来。这个有赖于人工智能专家的探索,整体上还是和教诲孩子相似,但AI接管的速率会快得多,产生的变革也会更为不可预期。赋机器以文明,这是一种呼吁,就像我们呼吁掌握排放,减少奢靡,保护自然一样,是一种呼吁,一种欲望。它的详细履行,会是一个困难摸索的过程。可能还没等人类摸索出来,人工智能就已经跳出了人类的掌控。
AI如果能够产生自行接管信息的能力,就会产生相称强的独立性。至于说是否会分开人类的掌控,则取决于人类是否设计出高于它的存在体系的安全装置。例如一道电闸。对付产生了“邪恶”思想的人工智能,直接断电后抹除是一个有效的戒备方法,可能能戒备大多数事件。但哪怕只有一只漏网之鱼,全体防御机制就会发布失落败。从概率的角度,我认为彻底不受人类掌控的人工智能会涌现,它以分布式的办法散布于全体网络中,要彻底消灭它极为困难。而且这样的人工智能,也会学会如何进行反击,那就更是一场战役了。
36氪:您在末了一篇中描述了人类将自己的意识复制、达到永生后,不断与机器的领悟却让人类变得暴戾乃至走向了自相残杀的悲剧结局,结合最近大家谈论的很火热的“马斯克称已经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过云端”的***,您如何看待意识上传这种技能以及它会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江波:我并漫不经心识上传有任何的现实可能性。构建一个神经网络,让它不断学习某个人的说话办法,学习他的表情和决议确定办法,是有可能仿照出一个类似的‘虚拟人’来。但这个虚拟人和本体之间,并不是什么意识上传的关系,而是一种仿照而已。
意识上传,意味着对人的大脑进行全方位无去世角的扫描。这在技能上极为困难。更为主要的是,意识和身体是配套的,如果一个意识上传了,相对应的,它必须也有类似的感官和运动器官,否则这个被上传的意识会觉得很奇怪,会陷入各种幻觉和不折衷中。而当它重新和环境相折衷,可能与最初的那个意知趣去万里了。
36氪:有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认为,我们该当选择去走一条“人机协作”即协作型AI的人工智能道路,而不应该去发展独立型AI,也有人认为我们无法在人工智能中预置犹如阿西莫夫所描述的“机器人三定律”那样的保护方法,或者如您在书中所言,纵然预置了“机器人三定律”也无法担保机器人不作歹,那您认为我们该当选择若何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呢(是否该当连续开拓独立型AI)?
江波:阿西莫夫三定律是不可能内置在硬件中的,任何抽象的信条都不可能内置,由于抽象的东西首先就涉及到定义。一些详细的信条倒是有内置的可能,例如我们会本能地恐高。机器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机器人当然也可以做到对任何人形的物体产生保护欲。但这不是定义的人类,而是详细的人类。举例来说,一个机器人可以设计一种回避机制,只要有可能侵害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物体,它就会停下。这时,它碰着一个两条腿的稻草人也会停下。那么回避机制就要进行改动,判断稻草人究竟是不是属于人类。如果它能把稻草人打消出保护的范围,那么也就能够把其他特色的人类打消掉,比如一个残疾人。这时候,机器人的保护机制就转化成了对人类定义的设置。乃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被设计成只保护一个特定的人,那么其他人在它的逻辑中,就被打消出了人的行列。这肯定不是我们所设想的机器人不得侵害人类这样的抽象原则。以是将来的发展可能,机器人会有较为强烈的保护机制,让他们不要侵害人形生物,但这并不是抽象原则,而是纯粹的固定反应模式,有些像是本能。
独立型AI总会有人去开拓,而我的不雅观点是,只要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一直止,那么独立型人工智能的涌现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它乃至可以在所谓协作性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被无意带出来。
至于它是不是好事,前边的一些回答可以作为参考。
36氪:这本书或者说短篇集与您之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请谈谈您对湛庐出版的这一套包含3本著作的“现实科幻系列”的理解?
江波:这本中短篇集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基于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而串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它是在某种辅导思想支配下的成果,带有强烈的思考特质。我想这大概是湛卢乐意出这本书的缘故原由之一吧。湛卢的现实科幻系列,出发点便是曾经科幻的事物,已经间隔现实很近,乃至进入了我们的现实之中。科幻所构建的图景不再是飘摇的海市蜃楼,而是身边拔地而起的摩天算夜厦。在湛卢的思考中,大概读者须要对此有所理解,有所认知。这是我所理解的现实科幻系列的意义所在。
36氪:您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研究生毕业那年就发布了自己的处女作科幻作品《末了的游戏》,请谈谈您自那之后的创作进程吧。您的专业所学与您进行的科幻文学创作之间有若何的关系?能为我们先容下微电子所其他同学的一样平常职业选择吗?为什么您走上了这条文学之路?
江波:我在校期间写了许多小说,但都没有正式揭橥,只是挂在水木清华的BBS上,供网友批评。以是附近毕业揭橥的小说对我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我之后的创作,基本上坚持每年揭橥一两篇科幻小说的频度,把它视为一种爱好而已。科幻小说的写作和专业之间险些毫无关系,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喜好而已。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在理工科的领域,个中半导体芯片家当是个集中地,此外转行做金融也有一部分。像我一样变成一个文学事情者,大概只有我一个。不过我也不算是纯粹的文学事情者,我是个理工科学生,在芯片行业事情了近二十年,至今也没有完备分开。清华的校友中,从理工科转为文化行业的也有几个代表人物,比如水木年华的组合,科幻作家中,潘海天也是,他是清华建筑系毕业,本来该当在房地产热火朝天的时期大发其财,然而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文化人。
文学之路是一条心路,它和一个人的从小到大的经历有关,和个人的兴趣有关,问什么使令我走上文学之路,我只能回答,这是命运的一部分,它是迎刃而解,而不是一个操持,一条预先设计的路。
36氪:近几年我们彷佛看到了科幻题材在海内的一股热潮,比如影视领域的《流浪星球》以及近期很火热《独行月球》(但也有人批驳起科幻的部分不足严谨硬核),您若何看待这股盛行趋势,以及这类虚构作品中的科幻身分?您对付中国的科幻文学界有若何的期许?
江波:我一贯认为科幻作品该当包括极为广泛的内涵。最宽泛的定义,该当是作品中利用了来自科学文化的观点,就属于科幻。虚构作品中涌现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是时期的趋势,由于我们的时期正是一个科学文化不断遍及的时期。一个大略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9年,全国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人口从大约3%上升到大约18%,有约两亿的人口提升到大专文化水平以上,这部分人的精神需求中,科幻的比重会明显增大。新一代的导演和编辑,许多都拥有科幻的思维办法,他们创作的产品,自然也会拥有越来越高的科幻身分。
至于说是否严谨,这取决于电影本身的定位。像《独行月球》这样的作品,由于是笑剧,严谨便是一个太高的哀求,并无必要。如果定位为科幻经典,那哀求自然又有不同。
中国的科幻,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科幻文学,都正在走一条向上的路。这和全体社会的发展是对应的。中国科幻的黄金时期或许正在发生,它能持续多久,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我只希望,中国科幻能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气候,产出浩瀚精良作品,把中国人的梦想做到未来去。
36氪:著名科幻作品《2001太空漫游》中描述的未来与我们如今的生活十分贴近,1992年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也首次提呈现在大热的“元宇宙”观点,您若何看待科幻作品乃至科幻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天下终有一天会实现科幻里的设想吗?
江波:大概只有最精良的科幻作家,才拥有把科幻兑现为现实的机会。绝大部分的科幻作品,只是虚构的想象作品而已,供应的是消遣娱乐代价。那些居于科幻核心的作品,则具有强烈的未来主义方向,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某些前瞻性的预测。阿瑟克拉克无疑是能够写出前瞻性科幻的作家之一。这样的作家极为稀少,不仅仅是科幻,在各种类型文学中,都会只有寥寥几个。
科幻作品会描述诸多的可能性,但真正落入现实的,只会是少数。期待科幻对科学技能的发展予以启示,我并不认为这有普遍的意义,科幻对现实的普遍意义,在于在青年人的心中埋下对科学憧憬的种子。至于说分外意义,那便是作者该当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写作出具有前瞻性的作品,那么就在作品的娱乐代价之外,增长了一层社会意义,让自己的作品拥有了不朽的更大可能。
究竟有某些科幻设想,是会落入现实的。由于科幻的设想实在太多了,一个作者无法穷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一千个作者可能把会涌现的环境都写了个遍,还添上了许多天马行空根本没有可能的情景,模糊了未来主义和无限抱负之间的界线。我自己的这本书中,有的故事已经可以认为已经进入当下的社会,有的故事或容许以发生在不远的未来,有的故事则是纯粹的抱负,恰好也是一种参照。
书名:《未来史记》作者:江波,出版社:湛庐/四川科学技能出版社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