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价值不雅观_机械人_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最近成了热门话题。这跟机器人、打算机、互联网技能以及神经科学的新发展有关,其余,便是间隔预言中的奇点(认为届时智能打算机将超越人和替代人)来临仅剩30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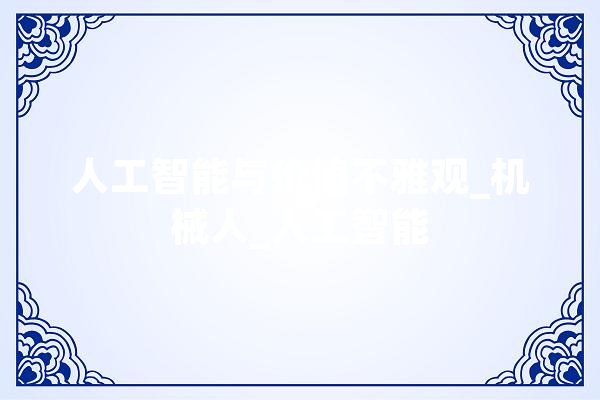
这是一个很科幻的话题,最早的谈论要追溯至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天下上第一部当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讲的是人类能够在无机质材的根本上,造出跟自己一样的,却又具备超级功能的生命体,虽非人工智能,却蕴含了干系母题,即人造人的命题。
最早明确涌现机器人这个名称的艺术作品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话剧《罗萨姆万能机器人》,韶光是1921年,这是不折不扣的人工智能作品了。该剧讲述人类大量制造机器人奴隶来从事繁重劳动,后来在同情它们的人类的启示下,机器人对自己的地位心怀不满,逼上梁山,杀尽人类。
但统治天下的机器人痛楚地创造它们无法繁殖后代,绝望中,一对男女机器人奇迹般进化出人类最伟大的情绪——爱。新的亚当夏娃出身了,天下得以延续。
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人工智能就绕不过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人能否造出具有很高智力的新型机器,它们能否拥有人类一样的大脑,乃至更厉害;二是机器会不会具有情绪,乃至得到自我意识;三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是个什么地位,法律上能否接管它们是人,它们是否拥有人权;四是它们会不会取代人,会与人类和谐相处还是背叛和消灭人类。
后来的科幻小说中涌现了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都表示了这样的主题。最有影响的是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为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设定了三条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侵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侵害;第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这三条法则排列组合,演绎出千奇百怪的故事。这部成功的科幻小说也反响出:西方在谈论人工智能时,一开始就有底线思维,要对它进行限定。
直接以“人工智能”命名的科幻电影是斯皮尔伯格2001年推出的《A.I.》,我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电影。影片描写了一对夫妇,在他们10岁的孩子因车祸成了植物人后,购买了一个儿童机器人当儿子养,以缓解内心苦楚。这个机器孩子的形状、智能和情绪跟人一样。但有一天,真孩子清醒了,回到了家庭,对机器民气生妒忌。于是,父母把机器人弃至野外。这使机器人孩子很痛楚,到处流浪,又遇上反对机器人的人类在捕杀机器人,场面惨烈残酷。
后来,这个机器人儿童侥幸逃脱。他想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孩子,能回到人类母亲自边,于是他去了纽约,找到了制造他的科学家。当他看到实验室里摆满跟他一样的机器人,才知道自己的确是机器人。但设计师说,你懂得了爱,就已经是人类了。
然而,他对这种哲学上的回答仍旧困惑,就跳海了,成了第一个自尽的机器人。2000年过去了,人类灭绝,外星人来到地球,找到了这个机器人,提炼出它的想法,启动了它,为了知足它的心愿,又为它复制出早已去世去的妈妈,但这个相逢只能坚持短短一天。机器人终于作为一个真正的孩子回了家。
这部影片探索了人与机器人的地位问题,也谈论了爱和灵魂的问题,具有哲学和宗教意义。
近些年,西方关于人工智能的小说大概多,不少是从近期可能实现的角度去谈论的。比如预言会产生陪伴型的人工智能,像宠物狗一样。还有咨询型的,可以帮你选择信哪种宗教。有的人工智能会诱惑你去购买特定的商品;不少人工智能被授予学习和复制的本领,可以自主进化。
有一个小说,讲科学家仿照出了跟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思维相似的人工智能,结果它险些赢得总统大选。很多作品认为人会离不开人工智能,末了与它融为一体。这里面除了技能,还包含了代价不雅观,这是西方科幻最核心的东西。
那么,在中国的科学研究中,是否看得到代价不雅观呢?是什么样的代价不雅观呢?我们的界线在哪里?这是让人很感兴趣的。
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中有一个叫做哈尔的人工智能形象,末了疯掉了。这个哈尔是按西方人的或者弗洛伊德式的人格来塑造的。那么,未来的人工智能,会否被授予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呢?
来源:2015年07月0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
《环球》杂志授权利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
来源:新华社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