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将带来一场大年夜浪淘沙式的“洗牌”_人工智能_主体性
作者:王琦(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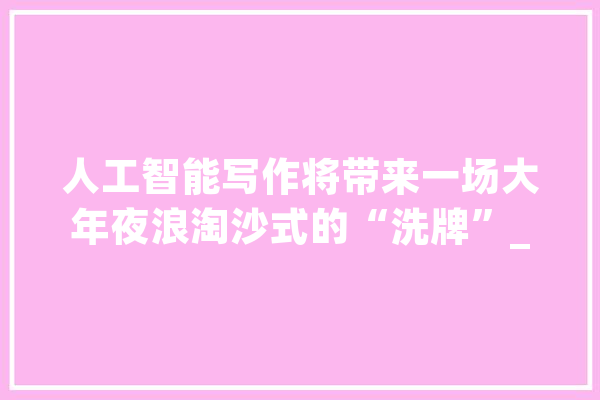
伴随着人工智能(AI)技能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写作日益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热点话题。网络文学作为当代科技与文学结合的产物,与人工智能写作的交叉领悟尤为深入。网络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写作紧张表现为一种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而独立创作的“智媒生产”,即人工智能通过在海量的文本数据中演习,总结写作规律,继而创作出具有连贯性的故事构造和风格化表达的网络文学作品。人工智能写作目前已初具标准文本的逻辑规范,并在某些类型写作与运用文体上已超过一样平常的人类水平。为此,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因缺少必要的生存体验和情绪共鸣无法写出真正具备生命温度和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写作的“非人化”征象引发了“网络文学创作是否将要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是否会闭幕网络文学”等现实社会焦虑问题。
人工智能时期网络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地位不可替代。上述征象的产生紧张源于人类担心自身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首先须要回答的是人工智能的实质属性问题,即人工智能是什么,它与人类存在若何的主体性关系?从词义上来说,人工是“人造”“合成”的意思,人工智能即与人类自然形成的智能不同,属于人造的或合成的智能,其目的便是要它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也便是说,人工智能实质上是人类聪慧的衍生物或者说是集成者,是一种“类人主体”。智能化程度较低的人工智能只能大略模拟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并不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或相等的创造能力。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不断发展极有分开人类掌控的风险,当下的人工智能已经拥有深度学习、不断自我进化、独立完成繁芜任务等能力,但是,人类始终是决定其深度学习、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功能的终极者。
人工智能写作的创作主体具有跨界领悟性。在高度精确的措辞模型与弘大的数据算法面前,网络文学创作边际已经呈现整合态势。如加拿大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通过文学原型论见告读者,文学中存在着可以独立交际且较为稳定的构造单位,不同的故事有共同的内在构造。但是,这种理论描述始终是抽象的,并不能真正辅导一位作家乃至一部作品的出身,它更多的是见告读者该当若何去阅读文学作品,文学写作依然被当作属于少数具有文学天赋的人才能从事的职业。基于对文学原型措辞模型和算法机制的闇练节制,人工智能写作不仅能将文学原型具象化,还能结合特定的情境对文学原型进行丰富、加工乃至改造,进而直接写出一部完全成熟的文学作品。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文学写作产生了颠覆性意义。只管网络文学从出身开始,机器化、套路化、程式化便是其为人所诟病之处,但网络文学毕竟也须要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参与,读者还是可以从措辞表达、故事框架、思想表达等方面分辨出作家的高下和作品的利害。人工智能写作则不然,如其演习得当,在节制大量语料和逻辑,并得到现实履历的根本上便存在创作出精良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从而对网络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性带来深刻寻衅,为网络文学创作者带来较强的危急感。
人工智能写作的网络文学创作主体性经历着双重洗礼。这种主体层面的危急感既是精神主体性也是实践主体性的。文学主体论强调的是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地位,尤其是强调人的精神主体性在实践主体性之前的优先性。在数智时期,“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受到人工智能的双面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化的过程中作家的精神主体性会失落落。人类在媒介中对信息的自主决策权转让给算法,AI技能代替了人进行内容的选择,兴趣方向的自主性并非完备自身建立,变相地削弱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导致人无法在文学创作这一精神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不雅观创造能力。另一方面,精神主体受限的同时,实践主体的地位也涌现旁落趋势。在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中,人由主体实践地位逐渐变成非核心参与者,人工智能的类人化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人”的一壁,人工智能的超能力正在取代人的创作职能,使得人在创作实践中的客体地位大于主体地位。进而言之,网络文学创作“非人化”导致人的精神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的双重失落落,将会使本就原创性不敷的网络文学面临创新危急,不断徘徊于故事的类型化与情绪的有限性当中。
然而,还应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写作推动网络文学创作主体性的开释。在人工智能时期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技能并不是大略的、线性的对抗,而是领悟了互构与互训。既要看到“人”主体位置也要承认其客体化处境,人不仅仅是发号施令的单向度主体,也成了与智能技能共生的有机体,承认创造主体在人工智能时期下的多重受动性。根据部分网络作家的描述,人工智能不仅会帮助他们进行诸如资料查询、方案构思等前期准备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场景想象和人物刻画,快速、准确地完成文本编辑与校正,还能在后续图书推广过程等分析市场数据、市场趋势和读者喜好,从而更快捷地完成作品市场推广。从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媒介技能的不断进步并未让文学消逝,相反可以为文学的持续性成长供应新的活力和动力。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是技能,技能是人类文艺创作中的外在要素而非全部,更不能取代人类文艺创作内在的精神特质,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会开释人类主体性的巨大潜能,从而真正实现“人机协作”。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媒介革命及新的媒介文化将会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倒逼网络文学创作者深化生命体验、提升精神素养、追求文艺佳构,从而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去芜存菁,实现经典化。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