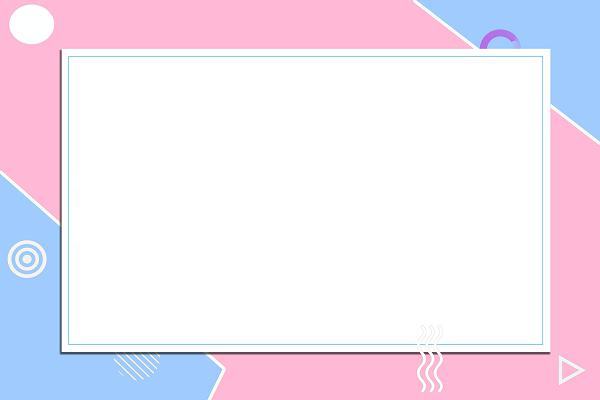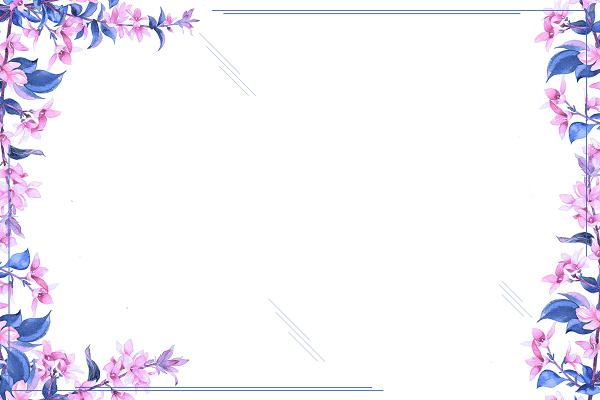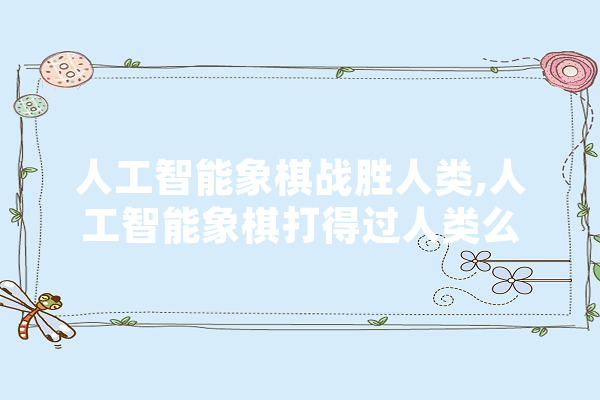对话社会化人工智能:弈棋的“读心”机制及意义_国际象棋_弈棋
个中,人类在对弈过程中展现的“读心”(mindreading)能力尤为值得关注。“读心”是指理解他人的各种生理状态(包括信念、态度、欲望等),是社会交往的核心能力。在社会化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让机器人学会“读心”,是实现高效人机交互的条件,是未来社会化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之一。国际象棋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果蝇”,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认知科学研究者对“读心”能力和国际象棋的研究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均取得了大量卓越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两者相结合的研究依然百里挑一。我们认为,磋商弈棋的“读心”机制,不仅能丰富“读心”能力的已有研究,而且将为促进动态交互过程生理机制的研究供应若干证据,并为人类开拓社会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读心”模块供应多少理论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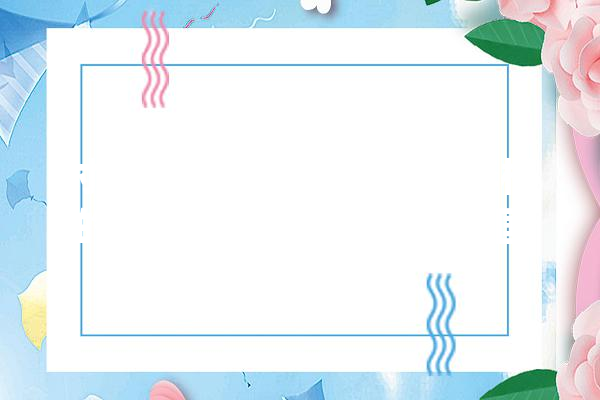
一方面,有关“读心”的早期行为研究紧张形成了一系列经典任务范式,同时揭示了“读心”能力的发展轨迹。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转向关注“读心”能力发展的影响成分。例如,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及经颅磁刺激(TMS)、事宜干系电位(ERP)等技能手段,研究者创造了“读心”的脑与神经机制。“读心”能力的加工紧张对应的脑区位于内侧前额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双侧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和内侧顶叶皮质(medial parietal cortex),且干系脑电身分在韶光窗口上常日晚于在刺激涌现后200ms,并一贯持续到800ms旁边乃至更晚。
另一方面,虽然国际象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鲜有研究关注国际象棋对非智力成分的影响,而后者正好是人类应对繁芜社会交互环境的核心技能。国际象棋作为一种零和博弈任务,双方棋手不仅须要对盘面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推理、决策,同时也须要投入大量精力来获取对手的生理状态(包括低阶的眼神与表情识别、动作意图,以及高阶的欲望和信念),并对其进行预测,从而实时优化自身的策略。这一过程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场景高度契合,其理应有“读心”能力的参与。
直到最近,上述履历推理得到了干系实证研究的支持。鲍威尔(Powell)等人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fMRI研究首次创造,国际象棋对弈过程与“读心”任务可能激活相同的脑区。陈巍等人2019年采取视觉不雅观点采择任务(visual perspective taking tasks)评估11—12岁有履历的棋手和未接管国际象棋演习的同龄人的“读心”成绩。在该任务中,被试须要判断他们自己和任务中虚拟角色的视觉视角是否同等。结果表明,国际象棋选手的表现优于非国际象棋选手,但当任务须要较少的实行功能时,这种上风就消逝了。其余,与低实行功能需求的非棋手不同,在这种情形下,棋手并没有表现出更好的视角采择。这些创造表明,长期的国际象棋履历可能与儿童在不耗尽认知资源的情形下更有效地接管他人的视角有关。
上述研究结果为思虑“读心”能力与国际象棋之间的关系供应了宝贵的研究数据,并为对话社会化人工智能供应了丰富的启迪。正是由于有了“读心”作为对弈的社会认知根本,才使得弈棋游戏许可我们在社会互动中实现虚拟性的“反复失落败”,在持续反复的“去世亡”与“重生”循环中,我们走向成功。只管应对与环境和他人的互动失落败彷佛是传统的人工智能设计须要极力避免的,但是大脑层面的失落败与成功可以带给我们同样的“褒奖”。特殊是当我们快要成功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勉励我们连续考试测验下去。因此,从弈棋过程的“读心”活动中不难创造,并不是只有成功的互动才能够勉励学习,失落败也是弈棋学习的一部分。失落败是学习者测试自己习得内容的一种主要办法,认知主义者主见知识的载体是符号表征,而符号表征可以具有明确的定义。以过去基于认知主义的机器人为例,全天下最聪明的大脑为他们编写了程序,授予它们办理某类实际问题(步辇儿、抓握)的能力(算法)。但在实际测试中一旦所面对的任务发生了些许的改变(园地变革、目标物体改变),这些机器人就手足无措了。具身机器人则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这类问题。这也是从认知主义转向具身认知的一种新的洞见,即周遭天下中的信息对基于不同既有认知构造的工具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周围事物的表征办法在不同个体中并不完备同等。具身机器人正是放弃了将程序员编写的抽象表征作为固有的知识内容,让机器人具有一些初步的觉得运动能力,与周围环境互动并逐渐产生属于自己的“认知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机器人制造者不再对机器人的问题办理议方案略进行预先的规定,而让机器人在探索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问题办理议方案略。
这一问题在人工智能中被称为观点接地(symbol grounding)。在对弈及其干系的下棋学习过程中,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弈棋观点知识的通报过程中,教练员对知识的阐述携带着属于自己认知构造中加工的痕迹。对付弈棋学习者,这些观点可能须要有不同的表征办法。如果强制学习者按照某种办法去进行表征,会影响该知识的存储与运用。在对弈过程中,教练员与棋手建立共享的生理状态并持续交互,棋手与知识的关系也发生了变革。棋手不再是被动去影象、剖析所吸收到的信息,而是试图主动构建自身与新知识的联系。终极,上述知识会以某种模块特异性的办法参与到弈棋的“读心”活动中。这意味着社会化人工智能的设计同样必须深入思考观点接地问题。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方案项目“国际象棋演习对小学生生理理论的影响及其提升研究”(18NDJC112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大脑、心智与教诲研究中央;浙江大学措辞与认知研究中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奇扬 陈巍 赵翥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