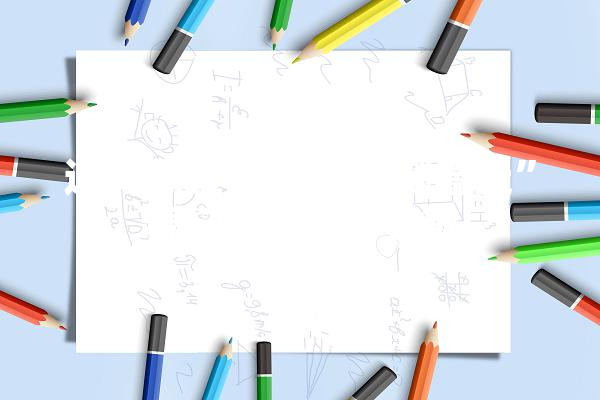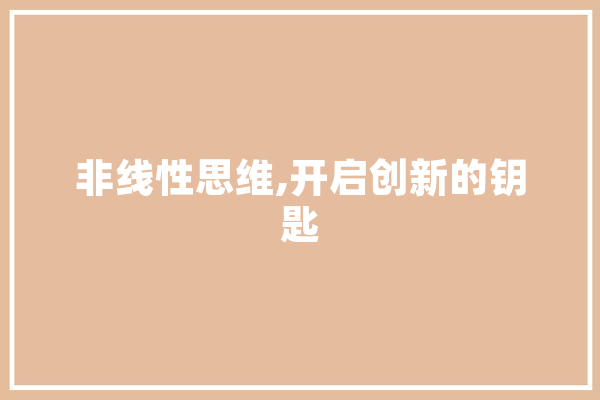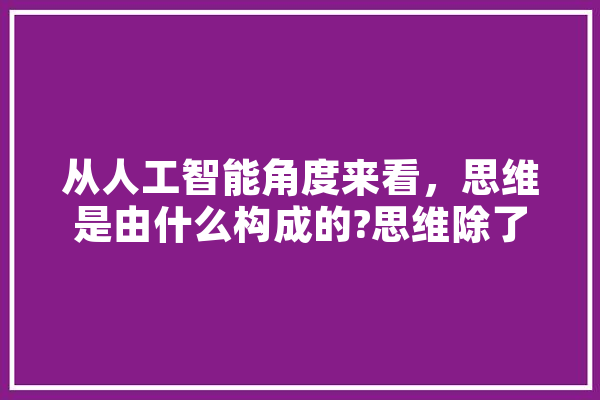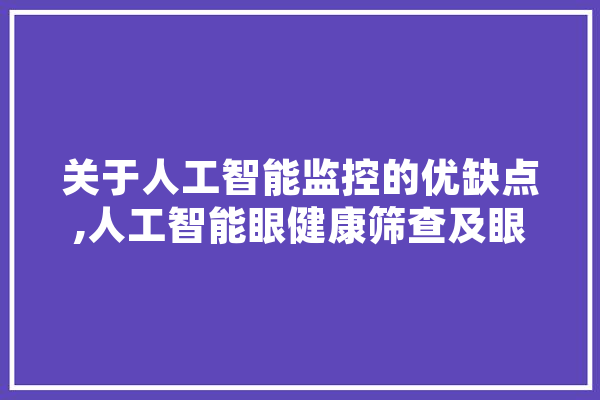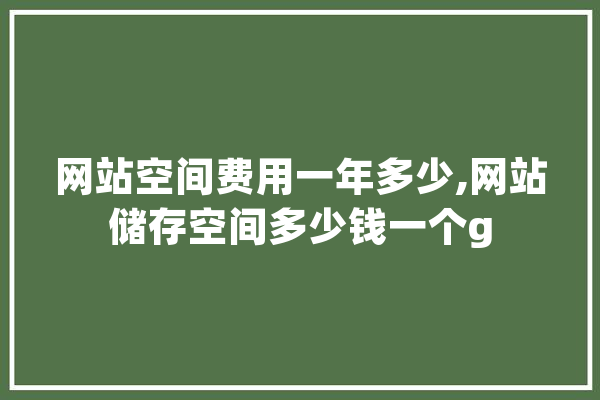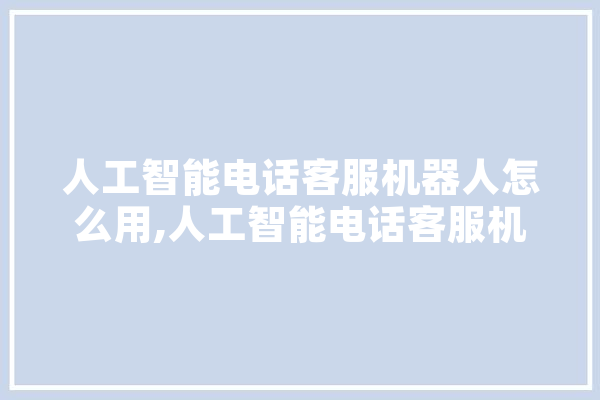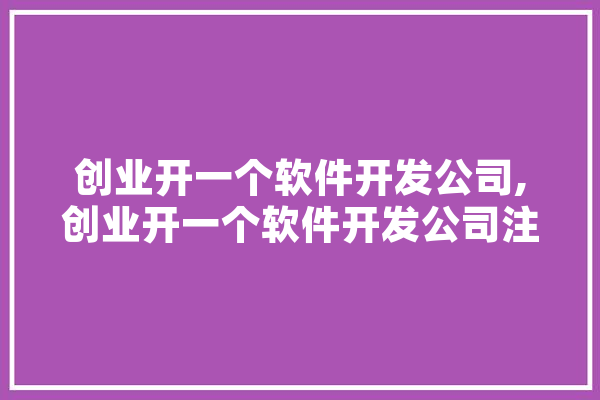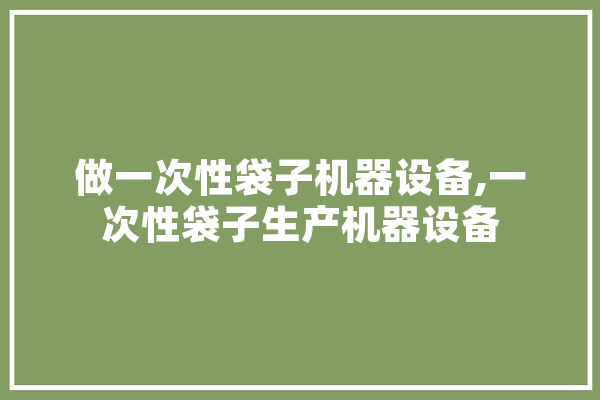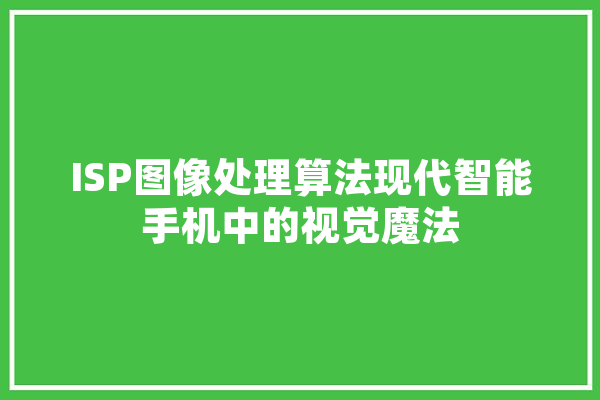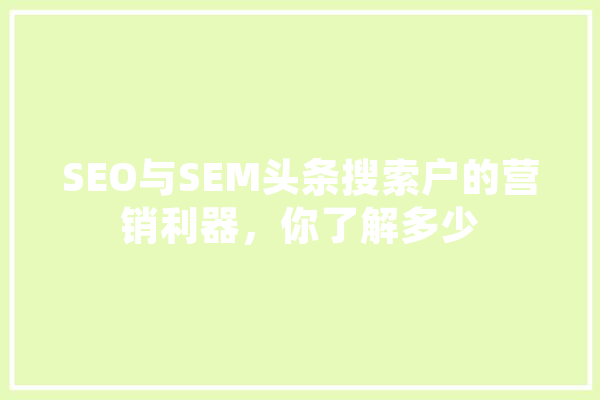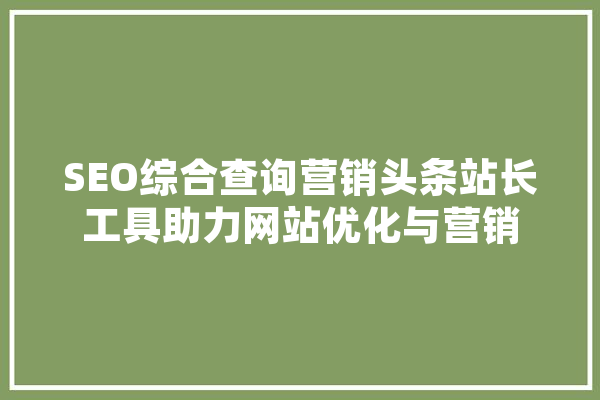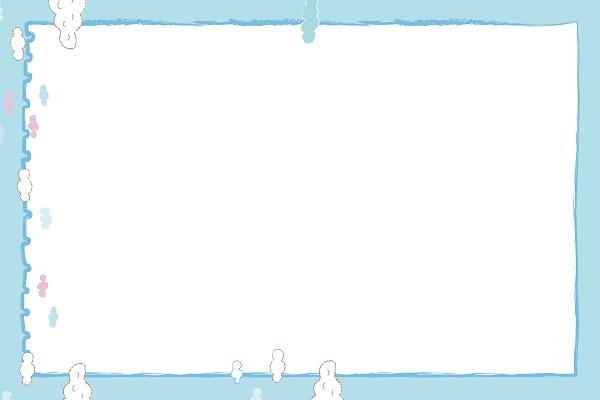埃里克·奥尔森:人工智能的形而上学_思维_人工智能
本文作者埃里克·奥尔森认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思维自身的实质是否妨碍思维涌如今打算机中。二、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工思维者。前者可称为人工思维问题,后者可称为人工思维者问题。本文即关注后者:人工思维者究竟是打算机,还是打算机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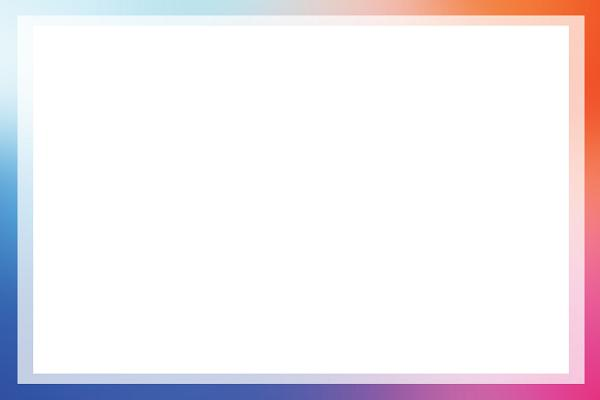
奥尔森剖析了三种不雅观点。第一种是打算机硬件不雅观,认为人工思维者便是打算机或者打算机的一部分。他认为打算机硬件不雅观是对人工思维者问题的最好回答,但这一不雅观点并不随意马虎让人接管。对该不雅观点最明显的质疑是它违背了思维存在者的持续性——关闭电源、删除数据后,打算机的硬件仍会存在,但程序停滞运行却会使这个智能的存在失落去智能;数据迁移会迁移走打算机的生理属性,但硬件却不必随着迁移。这些质疑正在匆匆使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打消掉关于跨韶光人格同一性的主导不雅观点。第二种不雅观点是思维—主体极简主义,即在思维的存在者必须由且仅由直接参与其生理活动的所有事物构成。但该不雅观点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很难说清楚某物直接参与某个存在者的思维或其他活动相对付间接地参与或完备不参与的差异。而严格来说,很有可能没有存在者能参与一个以上的生理活动,由于没有两个生理活动会具有完备相同的原子参与个中。第三种不雅观点是对人工思维者问题持宽松态度。该不雅观点的缺陷就和它避免争真个优点一样明显: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探究会由此令人失落去兴趣。
奥尔森认为,如果人工思维者没有令人满意的阐明,或者至少没有显示有这样的阐明存在,我们就无法确立人工智能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玄学
文/埃里克·奥尔森
译/王世鹏 张钰
什么是人工智能
很多人都相信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仅凭着以恰当的办法对一台打算机进行编程,就有可能产生智能。或者,单凭编程可能还不足,这台打算机的内部状态可能也须要以恰当的办法与它的环境联系起来,让这台打算机有类似知觉(perception)一样的东西。而且,这台打算机可能还须要引起一些可以感知的变革来显示它的智能,让这台打算机有类似行动(action)这样的东西。或许人工智能只能以一种机器人的形式涌现。我们假定,所有这些附加的哀求都可以知足。
我用“打算机”来意指电子的数字打算机。“人工智能”常日指的是电子智能,而不是像科学怪人那样由人工创造的生物智能。我用“智能”来意指信念、希望、感情、觉知(awareness)等统称为思维和意识的一样平常生理征象。有些生理征象可以通过打算机编程天生,但有些生理征象就弗成,信念和希望或容许以,但感情和故意识的觉知就弗成。这便是有关这些生理征象的一个主要的事实,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主要的事实放在一边。当前我的兴趣在于这样一个不雅观点:对打算机编程确实能够产生生理征象。
“人工智能”这个术语还有别的意思。常日,它指的都是打算机中的那些我们可称作智能行为(intelligent behavior)的东西:便是要让机器去干这些人类只有利用生理能力才能干成的事,比如识别垃圾邮件、下棋、开车等。这个术语也能意指通过对打算机编程来仿照或者模拟生理征象。在本文中,人工智能是指在打算机中产生真正的思维或者意识,凡是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不雅观点,都被称作强人工智能(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思维与人工思维者
一样平常认为,要知道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只须要考虑生理征象自身的实质。我们须要确定的是,生理征象的实质是否哀求生理征象具有一种分外的基质(substrate)。我们知道,生物有机体中能够产生思维和意识。那么思维和意识的实质中是否有什么东西,妨碍了打算机中产生思维和意识呢?有人相信,生理征象的特点完备就在于其因果浸染,这便是所谓的“功能主义者”。他们还辩论说,基质并不主要,只要它能干事就好。思维就像是计时——任何一种东西,只要它会按规则的韶光间隙发生变革并记录下已经历经由多少次这样的变革,就都可以用来计时。至于这种东西由什么构成,或者这个过程中是否涌现齿轮、沙子、水或电子器件,都是无关紧要的。另有一些人会说,生理征象不像计时,由于生理征象所须要的不但是让行为具有适当的因果浸染。这些哲学家对人工智能常持疑惑态度。
但是,即便表明了生理征象的实质中没有东西将生理征象束缚在生物基质当中,这也并不敷以确定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要确定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还须要更多东西。不但一定要有人工思维或者人工意识,而且一定得有什么东西作为思维或者意识的主体。有思维或者意识,就有在思维或者在意识的东西;正如有生命,就有活着的东西,有运动,就有处在运动中的东西。那么,有人工智能,就必有一个人工的智能存在者,即由于打算机的浸染而且有智能的东西。
以是,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思维自身的实质属性中是否有什么东西妨碍思维涌如今打算机中。我们可称之为人工思维问题(the question of artificial thought)。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工思维者。我们可称之为人工思维者问题(the question of artificial thinker)。这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人工思维者会成为何种实在。除了生理属性之外,人工思维者还会具有什么属性?它会是物质的东西吗?若是,它由什么物质构成?若不是,它又会是何种非物质(immaterial)的东西?如果不是物质,它会由什么构成?
这问题必有一个答案。就像自然思维者那样,人工的智能存在者一定得有某种实质。它一定或者完备由物质构成,或者不由物质构成。若是前者,那么某些分外原子(或许是打算机硬件或者机器人设备的某些小的部分)就会一次次构成它。哪些原子才是人工的智能存在者呢?答案不一定要精确。可以有一些原子,它们既不明确是又不明确不是人工思维者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原子可以既非明确是又非明确不是你我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哪些原子(若有的话)是它的部分,哪些不是它的部分,哪些处于其间状态,总得有个说法。如果人工思维者不是由物质构成的,那就得解释其非物质的实质。
要评估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我们不但要对思维和意识自身的实质有所理解,还要理解在思维的和故意识的存在者的实质。而且,正如有情由质疑是否一台打算机所做出的任何事都可以算作是真正的思维或者意识,同样也有情由质疑对人工思维者的玄学实质的解释是否可以接管。
险些所有关于人工智能可能性的谈论都专注于人工思维问题。与之相反,人工思维者问题则乏人问津。哲学家们通过追问是否打算性能做的任何事都可以算作思维,来追问人工智能是否可能,但对付这些“打算机”究竟是何种东西,哲学家们却险些一声不响:人工思维者究竟是打算机,还是打算机程序?
关于人工智能的谈论,常常在叙事办法上遮蔽人工思维者问题。对人工思维问题的一个范例陈述是问,“智能是否能够仅仅具身在系统之中,该系统的基本构造与大脑类似……或者它能否以别的办法来实现”。这就以两种办法让我们游离于人工思维者问题之外了。其一,它提到人工“系统”,“系统”是一个能够指代险些所有东西的模糊术语(类似于“基质”和“媒介”)。问“这个别系”在某种情形下是否具有智能,不过是在问某个有理解力的工具是否具有智能,而没有进一步显示出它不属于任何分外实在。这阻碍了我们对这个工具的更详细的追问。其二,它问智能是否“具身在”某物之中,或者在某物之中“被实现”。这并不是在问这东西是否事实上是智能的,而不过是在问它与智能的属性是否处在某种既密切干系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当中。即便知道了智能可以“具身在”打算机当中,也并没有见告我们这个智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表述办法是经由精心选择的,其目的便是为了既表述出人工思维问题,又不引发人工思维者问题。这并没有什么错,由于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问出所有问题。但是,这确实妨碍我们看到人工思维者问题的存在。
一定要有一个思维者吗
我曾说过,如果人工智能是可能的,那么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能够作为这个智能的主体,正如有思维就有在思维的存在者。多数承认人工智能的人都接管这个主见。但是他们该当接管吗?难道说,生命须要有活着的东西,运动须要有在动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在思维,又怎么会有思维涌现呢?如果是这样,人工智能就不须要有人工思维者,而其辩解者们就不须要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操心了。人工思维者问题也就不会浮现。
我认定人工思维要有一个主体,我也认定人的思维要有一个主体,两种认定情由完备相同。我相信现在我正通过书写来通报的这些思想,都是属于某人的思想,它们是某人的状态,或者某人正在从事的活动,这篇文章有一个作者,如果有什么存在者正在思维这些思想并将其写下来,那便是我,如果这些思想没有思维者,这篇文章就没有作者,推出的结论便是:我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什么类似于我这样的东西,正如不会有像牙仙子这样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不存在,你也同样不会存在。我相信我的确存在,也相信你存在。
但是,如果有可能在一台打算机中产生了思维却没有任何东西在进行这个思维,那也就有可能在一个人中产生思维却没有任何东西在进行这个思维。你我现在正沉浸于个中的这个思想就不须要有人来思维。即便我们不存在,事物同样会如此这般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事物不会向任何人这样显现。但是,如果有思维而无思维者,那就类似有征象而无任何存在者使得事物如此这般向其显现。而且,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会削弱我们相信自己存在的所有根据。
质疑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思维存在者的存在并不一定是猖獗的,正如质疑物质天下的存在也不一定是猖獗的。但是由于这些质疑缺少强有力的情由,因此我们就该当接管:我们存在,而且人工思维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拥有一个思维者。
打算机硬件不雅观
假定在恰当的环境中以恰当的办法对一台打算机进行编程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思维。这个思维的主体是何种事物?人工智能究竟让什么有了智能?
人工思维是由打算机的状态和行为构成的,有鉴于此,最明显的答案便是:打算机本身是有智能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是那些谈论人工智能的人最常见的说法,这些人通过追问打算机是否能思维来追问人工智能是否可能。他们认为这个主见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既不为其供应论证,也不考虑其他替代方案,乃至完备不打算弄清打算机是什么工具。但是,他们彷佛认定,如果打算机被恰当地编程,这时变得有智能的便是一块打算机硬件,即由东亚制造,由金属、塑料和硅制成的物理工具。
对自然智能的主体有一种富有魅力的描述与此类似:我们是生物有机体。生物有机体便是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我们看起来是物质事物,和有机体没什么两样。我们该当期望,人工思维者之于打算机,就犹如我们自身之于人类动物(human animals)。这样,如果我们是人类动物,那么人工思维者就一定是打算机。
人工思维者便是打算机或者打算机的一部分,这种不雅观点被称之为打算机硬件不雅观。我认为打算机硬件不雅观是对人工思维者问题的最好回答,但却不是一种随意马虎让人接管的不雅观点。最明显的质疑便是,它违背了关于跨韶光同一性(即思维存在者的持续性)的一些广为收受接管的不雅观点。
如果人工思维者便是几块打算机硬件,那么对一台打算机进行智能编程,便是要让先前无智能的存在变得有智能。而当程序停滞运行,这个智能的存在就会失落去它的智能,重新变回一块普通的打算机硬件。人工智能程序在我的台式打算机上运行一小时,就会让这台机器(或者这台机器的一部分)有一小时的智能。在这段韶光之外,它就和我的桌子一样没有智能。很明显,这肯定是错的。对打算机进行智能编程,不仅把智能的属性给予了先前没有智能的存在,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智能的存在者,这是一个诱人的设定。而关闭程序,抹除数据,就毁掉了这个智能的存在者,而非仅仅是剥夺了它的智能。然而,不管是运行还是停滞这个程序,却并不会创造或者毁灭任何一块打算机硬件。这样一来,从这个诱人的设定就可以推断出:人工思维者和运行于其上的打算机有着不同的历史,在人工思维者存在之前和闭幕之后,打算机都会存在。更一样平常地说,人工思维者和打算机的持续条件不一样:打算机关闭电源、删除数据也能存不才去,但是人工思维者就弗成。这样看来,人工思维者就不可能是打算机。
另一种诱人的想法是,人工思维者能够从一块打算机硬件转移到另一块打算机硬件。这不须要在物理上把一台打算机的零件拿掉,接到另一台打算机上,一次电子数据迁移就足够了。
此外,把一台打算机的所有数据迁移到另一台打算机,结果会导致第一台打算机损失它所有的生理属性,如影象、信念、偏好、认知能力等,而这些东西都被第二台打算机得到了。这会让第二台打算机产生一个缺点的信念:它便是第一台打算机,它做过第一台打算机在数据迁移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由迁移而产生的这个存在,还以为它便是原来那个思维者,那个在影象中的存在,而且这个存在连同数据一起从第一台打算机迁移到第二台打算机,这也是一个诱人的设定。
但是,这个想法也不能兼容于打算机硬件不雅观。你不可能通过电子数据迁移来移动一块硬件——金属和塑料制成的物理工具。按照那个诱人的想法,人工思维者具有的一种属性,任何一块硬件都不具有,那便是通过电子数据迁移来移动。打算机硬件不雅观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电子迁移能够把人工思维者从一台打算机转移到另一台打算机。
对付人类思维者的辩论比较熟习的那些人都知道,“动物主义”的不雅观点即我们是生物有机体,受到批评的情由与此类似。假定你的大脑被移植到我的头颅之中(或者你大脑中的生理信息被迁移给我),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人(即他)在生理上是与你而非我联系在一起的。他将拥有你在手术前的影象、信念、偏好及其贰生理属性。多数人都会说,他便是你——这场手术不会给我一个新的大脑,而只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但是,这场手术并不会给一个有机体新的身体,不会把有机体消减到大脑的尺寸,不会把有机体转移到新位置并用脑外部分的新添补来养活这个有机体。这场手术像肝脏移植一样,只是把一个器官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由此推出,人类思维者拥有任何有机体都不具备的一种属性,即可以通过大脑移植从一个有机体向另一个有机体转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类思维者就不可能是有机体。出于类似的情由,人工思维者就不可能是打算机。
一个在思维的存在者的续存(persistence)就在于某种生理上的连续性:如果一个在思维的存在者x现在存在,那么在另一韶光存在的某物y是x,仅当y和现在存在的x在生理上以某种办法是连续的。换言之,某种涉及生理连续性的条件对付一个在思维的存在者的持续存在(continue existing)而言,既是充分的又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任何涉及生理连续性的条件对付一个人类有机体或者一块打算机硬件的持续存在而言,是充分的或者必要的。
人工智能的支持者们当然要放弃生理连续性的不雅观点。他们接管的不雅观点是,对一台打算机进行智能编程不可能创造一个智能存在者,但是却能让一个先前无智能的存在变成智能的,而且删除干系的数据并不会毁掉任何智能存在者,只会让它处于无智能的状态。他们否认人工思维者能从一块硬件转移到另一块硬件,完备不理会心理上的连续性可能有多少,而且,他们会说,把你的大脑放进我的头颅中的结果,是你给了我新的大脑,而非我给了你新的身体。他们不认为有哪种生理连续性对付一个智能存在者的持续存在而言,是充分的或者必要的。我没有说这有什么错。我自己也反对生理连续性的不雅观点,由于我认为我们是有机体。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能打消掉关于跨韶光人格同一性的主导不雅观点,那会是一个主要的。
思维者的部分不雅观
目前为止,有一个我一贯忽略的难题,即确定人工思维者的空间边界或空间部分是什么的问题。试想我桌上的这台打算机是智能的。没有人会说我们常日称作打算机的这种东西的所有部分,包括键盘、鼠标、显示器和电源线,都是人工思维者的部分。那么什么东西会是人工思维者的部分呢?
如果有人工的智能存在者,而且人工的智能存在者是物质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必有一个答案。一些原子必定是给定思维者的部分,而其他原子不是。或者一些原子可能既不绝对是也不绝对不是给定思维者的部分。但是物质的东西一定具有边界,无论边界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
自然的智能存在者也有一个十分类似的问题:我们的边界在哪儿?哪些原子现在是我的部分,哪些原子不是?(以及如果我的边界是模糊的,哪些原子既不绝对是也不绝对不是我的部分?)这个问题也必有一个答案——暂且假设人类思维者是由原子构成的。
我们该当会期望有一条原则可以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阐明为什么在思维的存在者的边界就在他们所在之处,或是阐明是什么使某物成为某一思维者的一部分。如果我的手是我的部分而我的手套不是,那么必有为什么会这样的阐明。这不可能是没什么可多说的一个“原始事实”。一定有以下这一形式的原则:
如果在t时x是在思维的存在者,那么当且仅当……x……y……t……时,一定有y是在t时x的一部分。
如果自然思维者是生物有机体,那么要问确定自然思维者边界的是什么,便是在问确定有机体边界的是什么。对付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了一个答案:
如果在t时x是自然的思维存在者,那么一定有y是在t时x的一部分,当且仅当y在t时参与x的生命周期。
个中,生命周期是指从其周围接管粒子、将繁芜的生化形式加于粒子之上、而后又以降解形式将粒子排出的生物事宜或过程。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大体上是其生理的、免疫的以及代谢活动的总和。我的手是我的部分是由于它们参与我的生命周期——我的双手和它们的所有部分都得到我血液的滋养、并参与我的代谢过程。我的手套不是我的部分,由于它们没有参与我的生命周期。关于什么才算是生命周期涉及许多艰深的问题,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显然上述情形不适用于人工思维者。人工思维者的相应原则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我的打算机中心处理器是人工思维者的一部分,而键盘不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能想到的最好答案是这样:
如果在t时x是人工的思维存在者,那么一定有y是在t时x的一部分,当且仅当y直接参与在t时x的思维。
打算机键盘看起来完备没有参与打算机的思维。只管其电源参与打算机的思维——没有它,打算机无法产生思维——但与打算机数字电路的某些部分比较,这种参与看起来只是间接的。这表明人工思维者将会完备由电子元件和连接电子元件的电线所构成,人工思维者将会是由金属和硅所制成的、仅一两盎司重的一个薄的、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如果人工思维者的部分只是直接参与其思维的那些东西,那么我们该当会期待自然思维者也是这样。这一原则看来是由在思维的存在者的实质所派生的——与作为一个思维者意味着什么有关;与人工思维者没有任何关系。
这与前面的遐想相抵牾,即我们的部分由我们生物的生命周期所确定。但这并不令人惊异,由于之前的答案假定我们是有机体,而当前这种阐明彷佛打消了这一点,而是表明我的手不是我的部分。只管通过帮助滋养我以及为我供应触觉信息,我的手对我的生理活动有用,但它们的参与彷佛最多也只能算是间接的。在思维的存在者有手作为它的部分,这在玄学上是不可能的;可以推测,除了我的大脑以外,我的其他所有生命器官也都同样不可能。一些哲学家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并由此推断我们便是大脑。但这一不雅观点彷佛表明我大脑的许多部分并不是我的部分:比如我大脑的血管就彷佛只是间接地参与我的生理活动。我大概该当完备由神经细胞构成。(并且可能活性神经细胞也不是每一部分都会直接参与思维,而是只有传输旗子暗记的那些部分才会。比如,细胞核和线粒体的参与看起来只是间接的。)我们也该当是只有几盎司重的、薄的、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在思维的存在者必须由且仅由直接参与其生理活动的所有事物构成,我把这一不雅观点称为思维—主体极简主义(thinking-subject minimalism)。这一不雅观点在许多方面让人不安。一个令人担忧之处便是很难说清楚某物直接参与某个存在者的思维或其他任何活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原子直接参与某人的行走——相对付只是间接地参与或完备不参与来说?我疑惑是否有什么规则可以据以回答这个问题。
更严重的是,这个不雅观点很难一样平常化。若哀求参与任何活动的任何存在者,都必须仅由直接参与这一活动的事物构成,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存在者只有当它仅由直接参与不雅观看的原子所构成时才能瞥见,并且只有当它仅由直接参与影象的原子所构成时才能记得。神经学家见告我们,不雅观看与影象利用的是大脑的不同部分。这就表明直接参与某人的不雅观看的原子与直接参与此人的影象的原子不一样,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没有人能既瞥见某人的脸又记得此人的名字。参与看的事物,要么太大而无法记得名字,由于还有不直接参与影象的部分;要么太小而无法记得名字,由于没有把这些部分包括在内。或者当然可以两者都有。参与看的人和参与影象的人,由不同的原子构成,就一定是不同的人。这对付人工思维者可能也同样适用:任何瞥见名字的人工思维者都会不同于记得名字的人工思维者,正如会有不同的电路电位直接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
很有可能没有存在者能参与一个以上的生理活动,由于没有两个生理活动会具有完备相同的原子直接参与个中。看起来是某一个存在者在实行包含大脑不同部分的许多生理活动,而实际上可能是许多个不同的存在者——可能是既重叠又不同的——每一个只实行一个这样的活动。既有能力瞥见又有能力记得的“通用”思维者,将会是大略的(缺少部分)且大概是非物质的。
有可能思维—主体极简主义会以更为可行的办法而遍及,也有可能人工思维者的部分由实质上不同于极简主义的某一原则所决定。由于人工智能的支持者们相信人工思维者是物质的东西,他们将须要办理这一问题的办法。
宽松的态度
物质的东西是由原子构成的。以是对任一物质的东西而言,必有某些原子在一个给定的韶光是它的一部分,而某些原子此时不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人工思维者是物质的东西,那么哪些原子会是人工思维者的部分,这个问题必有一个答案。我曾说过,这个问题的答案该当在某一原则的辅导下涌现,比如思维—主体极简主义:某一人工思维者的部分仅为直接参与其思维的那些事物。但这一原则看上去让人无法接管,而又很难想到更好的。(这对自然思维者并不构成问题,至少如果自然思维者是有机体,那么什么东西是它们的部分与是否直接参与思维无关。)但是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而言,这个问题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试想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持宽松态度。假设对我的台式打算机进行智能编程后,打算机内有了各种各样的思维。那么这些思维的主体是什么呢?我们创造出的是什么样的人工思维者,或者是让什么样的人工思维者变得有智能了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大概并不令人感兴趣。可以说,思维者的候选者有很多,有打算机本身,包括鼠标、键盘、显示屏和电源线等。打算机有很多部分。或许也不是打算机的任何部分都能作思维者的候选者,或许我们可以打消键盘上的空格键。如果我们能让整洁划一的思维—主体极简主义不雅观念说得通,那么或许就不得不把打算机中直接参与思维和意识的那些部分席卷进来。但是更多限定就没有了。由这台打算机和这张桌子一起构成的事物是一个候选者;由本周的这台打算机的这个韶光部分和上周的那张桌子的那个韶光部分一起构成的事物,也是一个候选者(宽松态度包括对韶光部分与无限制的构成的承诺),等等。但是没有解释的是,这些候选者中谁是打算机中正在进行着的思维的思维者。它们都是思维者,它们之间并没有生理上的差异。
根据宽松态度,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付自然思维者也同样没什么吸引力。我的思想的思维者是什么?我是什么事物?这些问题同样也没有吸引人的答案。这里有很多候选项:我的大脑;我大脑的某些部分;这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各种“任意的、未分开的部分”,比如它的上半部分;由我的大脑和我的桌子所构成的事物等等。但谁也说不准这些候选项中哪一个是这些思想的思维者,他们都是这些思想的思维者。
我们利用人称代词及其干系名称与谓词时,至多有措辞老例的约束。我们利用诸如“我”和“奥尔森”这样的词指称有机体,而不指称大脑,不指称有机体的上半部分、不指称一个大脑和一张桌子所构成的事物。(大多数情形下,我们根本不会涉及这样的任意划分出来的实体。很明显我们忽略它们是有实际缘故原由的)这便是为什么说我有手以及说我有150磅重是对的;而说我有3磅重和我居于我的头颅中(没人曾在此见到过我)则是错的。类似的规则约束着这些一样平常术语的利用,比如“人”“哲学家”“印度教教徒”。不过,适用于我们依照老例利用的这些术语的存在者的生理属性与不适用于这些术语的存在者的生理属性之间,仍旧没有差别(至少只要这些存在者都包括直接参与干系生理活动的事物)。
以是我们不须要接管思维—主体极简主义。更笼统地讲,我们不须要担心人工思维者的问题。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在思维的存在者,它们的玄学实质并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兴趣的事实——或者至少没有比它们是物质的东西这一事实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但是无论宽松的态度有什么上风,它都与强人工智能合营不佳。这一态度的预设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思维。如果某一事物具有生理属性,那么其他许多事物,包括以第一个事物为部分的许多事物,就具有相同的生理属性。如果我的大脑是故意识的,那么我的上半部分、除我左手以外的我的全部、全体这个有机体以及由这个有机体和我的桌子所构成的这个事物就也都是故意识的。我不愿定该如何完全地阐述这一原则,但我们可以通过说生理属性是“大小不变的”(size-invariant)来概括这个原则。
一个问题立时涌现了:还有什么其他属性是大小不变的?比如质量就不是:我的上半部分、这个有机体和我的大脑都不能具有相同的质量。形状、颜色、位置、温度、硬度——以及很明显,尺寸——也都不是。很难想到我们熟习的什么其他属性是大小不变的,这彷佛是生理属性所特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使生理属性大小不变?
最顺理成章的缘故原由是,生理属性缺少质量、尺寸、形状以及其他常见属性的客不雅观实在性。我们创造这对付阐明和预期行为的目的有用,比如,将生理属性归属于某些实在,或者用丹尼特的经典表述“霸占对付它们的意向态度”,并且,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将生理属性归属于不同工具,可能是有用的,比如,处于不同目的而把生理属性归属于大脑而非有机体,或者反之亦然。只是这种归属的正误,与质量、尺寸或形状的归属的正误剖断办法不同。关于事物的生理属性,并没有无可动摇的事实,最多只有出于某些目的而将其归属于某物是否合宜的事实。
很少有哲学家接管关于生理的这种工具主义的或是反现实论的不雅观点。针对当前目标,说得更确切些,这种不雅观点可能会使强人工智能失落去吸引力。打算机究竟能否具有(或产生)真正的思维或意识,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于出于某些目的而说打算机具有真正的思维,用途究竟会有多大。而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气候学者明确地创造,说他们的打算机关于景象系统“知道”得比他们自己要多是有用的。我们也都创造,出于某些目的,将生理属性归属于复印机(“复印机认为没纸了,虽然我刚往托盘里加了纸”)以及恒温器(“创造房间温度升高了”)是有用的。科幻小说中最繁芜的打算机与19世纪的恒温器之间的生理差异,可能只是程度的问题,正如恒温器和人类之间可能有的差异一样。
工具主义的不雅观点认为,仿照智能和真正产生智能是没有差别的。对付心灵哲学而言,打算机可能并不比恒温器更有趣。如果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探究中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点,那就一定在于事实上哪些事物可以进行思维或是故意识的。而这与宽松的态度看起来是不一致的。
如果要有真正的人工智能,在恰当的环境中用恰当的办法对打算机进行编程必能天生真实的思维或意识。但这一真实思维或意识还该当有主体。而通过对打算机编程使哪种存在者有了智能,这很难说清楚。解释人工智能的主体是什么,并不像阐明自然智能的主体是有机体这么清楚自然。
人工的智能存在者一定是某种物质的东西。至少,任何推定的人工的思维或意识都是由某个物质事物的状态或活动构成的,而如果处于生理状态中或沉浸于生理活动时缺少思维或没故意识,那么这一物质事物将成谜。这可能便是为什么多数关于人工智能的谈论,都将人工智能使打算机能够思维看作理所应该的。
但是,这个不雅观点有悖于许多人想要谈论的人工思维者的续存条件:运行干系的程序时,人工思维者形成;关闭程序时,人工思维者受到毁坏,比如抹除干系数据。没有人假定我们称之为打算机的所有部分,包括键盘,便是由智能编程而得到的在思维的存在者的部分。人工思维者可能最多是打算机的某一部分,只是很难说它会是什么部分,而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
对付由此而有了智能的这种存在者,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阐明,或者至少没有显示有这样的阐明存在,我们就无法确立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这一点有待完成。我不是说它无法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这样的阐明对人工的和自然的思维者的实质都会故意想不到的影响。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注释已删除,学术谈论请以原文为准。配图源自网络资料,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