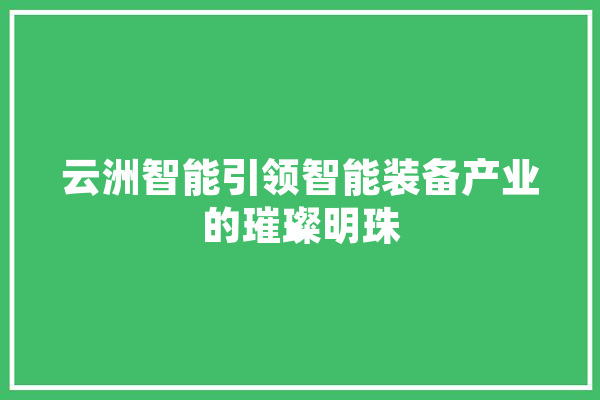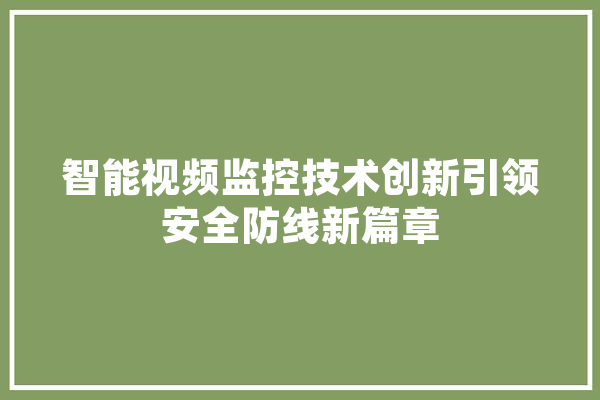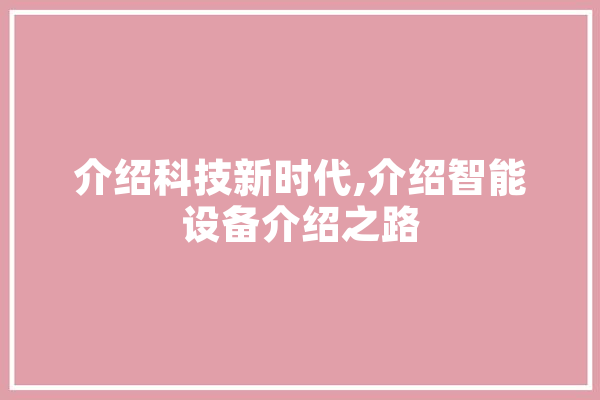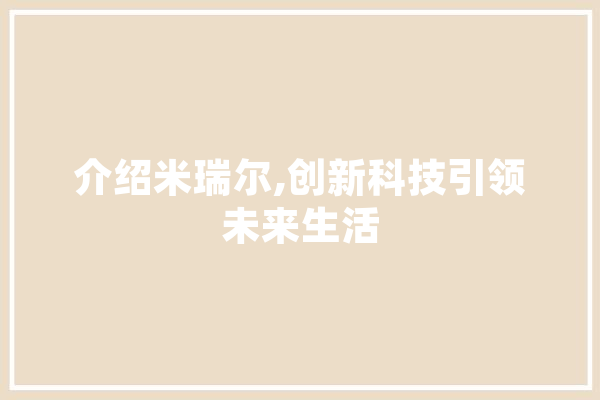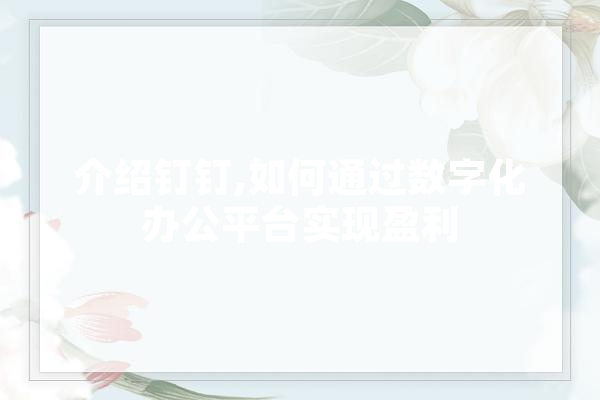《智能大年夜鞭挞》:少操心AI叛变多关心你爸你妈_互联网_智能
米歇尔一家不算大众意义上的“正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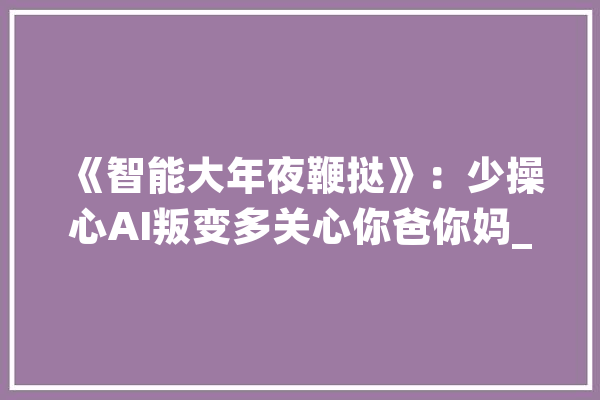
稀奇古怪的大女儿,酷爱拍小众电影;
社恐的小儿子,对恐龙爱到去世去活来;
母亲生来便有着盲目的乐不雅观;
父亲堪称万能工具人,但同时也是个“老古董”;
哦对了,他们还养了只天生斜眼的“舔狗”。
一家人此前所面临最大问题,是由于缺少有效沟通所导致的父女关系反面。
然而,就在一家人送女儿上大学的途中,人工智能“啪”地一下就叛变了,很快啊。
△ 机器人造型,有没有让你想到哈尔9000?
于是乎,看起来绝不靠谱的一家五口,只能姑且搁下不合,拜入混元形意太极门迫不得已拯救天下苍生于AI水火之中,顺道修补下千疮百孔的家庭关系。
无厘头的AI叛变+废柴伐木累拯救天下的设定,将这部名为《智能大反攻》(The Mitchells vs. The Machines,以下简称《智能》)的动画电影,送上了今年安妮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宝座。
△ 8项提名,《智能大反攻》斩获了“安妮奖最佳动画长片”大奖
素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安妮奖,是动画领域最大声誉之一。
多元类型+多维评判,构建起安妮奖货真价实的含金量。
△ 无论耳熟能详的主流大片,抑或是剑走偏锋的小众佳作,你都能在安妮奖中看到它们的身影
只不过去年的头号黑马《英雄同盟:双城之战》其实风光无两,在今年的安妮奖中,凭借9提9中的成绩和多年游戏积攒的人气,使得8提8中的《智能》,成了被人忽略的佳作。
《智能大反攻》这一充满老旧***腔风格的平庸译名背后,是绝对豪华的阵容:
《蜘蛛侠:平行宇宙》原班人马、Netflix + SONY加持,让本片在画风上要比《平行宇宙》中的“次元联动”更放飞自我。
温情的家庭主旋律中,暗藏对数字化浪潮的思辨。
为了操控人类,《智能》中AI的手段可谓丧尽天良,那便是——断网。
拔人网线,犹如断人奶水。很快,全天下便陷入了迷乱猖獗之中。
借此,《智能》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当代科技全部失落灵,你该如何生存?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或许我们要重新思考,科技与我们的关系。
伴随数次工业革命,人类在发明和操控工具方面,愈发得心应手。
是的,工具。
就彷佛过去父亲用DV记录生活,如今女儿用电脑和手机剪辑生活那般,听凭科技如何发展,“工具”都是他们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属性。工具,是身体器官的外延,帮忙人类完成肉体难以胜任的事情。
人对工具,应该有着绝对的掌握权。
但如今,我们逐渐依赖上科技。倘若出门在外手机丢失,可能会令一个人的生活陷入短暂的“瘫痪”——毕竟手机里集成了我们的全部“身家”。
△ 诸如《MAD MAX》这类迷影致敬彩蛋,电影中比比皆是
对科技在物理层面的重度依赖,势必导致生理层面的难以割舍。
《智能》中,科技巨子PAL创造的AI形象,从手机中那副千变万化的表情面孔,向其实体机器人形象迈进,倘若统统顺利,PAL会不断朝着“成为人类”的方向打磨AI。
从初音未来到《舰娘Collection》,从各大手机厂商的“智能语音助手”,到如今风头大火的Vtuber(虚拟主播&偶像)……无论是ACG圈子,又或者是主流商业文化,我们对“拟人化”这件事,仿佛有着异乎平凡的执念。
△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
这一点倒是不难明得:
在大家社恐、同时崇尚独自生活的时期,有这么一台设备:它会对你嘘寒问暖,知足你的沟通希望,帮忙你的生活起居。
最关键的:它不是人,但长得像人,听凭你摆布使唤,没有生理包袱。拥有这样的设备,何乐而不为?
因此,当今人与科技的关系,已经形成紧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将过多属于人类的情绪,投射到了科技上,而非将其视作纯挚的工具。
倘若真的存在AI背刺人类,我们除了错愕之外,或许在情绪上也会深受侵害。
《光环》游戏中,Cortana鞭策AI联合,背叛UNSC;
《智能》中,智好手机断掉了全天下的wifi。只管前者的故事更为磅礴,但后者“拔网线”操作,显然要更为戏谑。
“AI叛变”这一高观点命题,经由《智能》演绎,被奥妙转化成更贴近生活的忧虑:
没有手机和网络,我们该如何生活?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女儿在上面搭建起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自然原住民”,父亲对女儿和家人们沉迷手机的行为,嗤之以鼻:
把手机都放下吧!
“放下手机”背后的初衷自是美好,但问题在于……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
女儿通过社交网络,结交志同道合的好友;
母亲倾慕着自家邻居在个人主页里,po出的那一张张无去世角的完美日常;
社恐的弟弟可以像电话推销员一样找朋友,但是在真正喜好的女孩面前却涨红了脸;
父亲能做的:
在评论辩论社交与网络前,可以先回顾下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创建互联网的初衷:
他认为,互联网最具代价的地方,在于授予人们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
他希望万维网能够帮助人类整理他们现有的知识,供应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初衷,是想让陌生的彼此被联通、让远方的风景被瞥见、让微弱的声音被听到,搭建起平等互换的“去中央化”的平台。
只可惜,现状背道而驰,与《智能》所描摹的图景别无二致:
在潜移默化中,科技巨子将触手伸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过度美颜的生活,成为你心之神往;未经考验的碎片化知识,授予你自诩独立的信心。
殊不知,统统皆在“个性化推举”的算法操盘之下,经典猜想“缸中之脑”,被以“信息茧房”的形式呈现。
2019年4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名为《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的文章认为,互联网自主演化至如今的地步,或许意味着,这些“恶行”是互联网的“一定”。
不足为奇,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也曾对“技能中立”表示过疑惑。
浸淫网络天下太久,难免会戴上“互联网滤镜”,最显著的标志就表示在对身边亲朋的生疏——这也成为《智能》中父女间的核心抵牾:
两个人完备处在割裂的社友谊况当中,以自说自话的办法想要说服彼此,从未达成真正的共识。
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到过一个不雅观点,叫做“附近的消逝”,适可而止总结了《智能》中父女的抵牾。
互联网在联通陌生彼此的同时,消灭了你对身旁嫡亲的关注;微弱的呼声的确被放大了,但与此同时,本就振聋发聩的喊叫,也随之翻倍。
无论还是网络,四处都横亘着难以超出的鸿沟,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智能》中,拯救天下什么的,向来不主要大略,一起说学逗唱只是基本功。
毕竟对手是AI,以是你自然要用邪术打败邪术。
好在,父亲虽然对科技一无所知,但是确实……一窍不通。
这是全片最离谱、也最为民气酸的片段之一:
哪怕是身经百战的我们,都可能搞不懂层层繁芜的选项与步步陷阱的弹窗,更何况父母长辈呢?
父母也希望享受到数字化生活的便利,也希望通过互联网,看到远在他乡的我们;
然而于我们而言的大略触控,于他们而言,可能是高高的门槛,乃至是一座山。而更糟糕的,可能是大山还没攀爬,先落入数字陷阱。
利用工具都需付出一定学习本钱,是不可否认的客不雅观规律。
好在近几年来,政府推进适老化改造、整治互联网弹窗等乱象,企业也在投入开拓“关怀模式”,这一系列努力,都在尽可能降落老年人利用手机的学习本钱。
只可惜,“心有余而力不敷”,是摆在面前的另一个客不雅观规律。
我们的父母,究竟会像《智能》中反复涌现的恐龙那般,被甩在时期的车尾;他们究竟会撞上天花板,会有自己永久搞不懂、记不住的东西。
此时父母所须要的,不这天月牙异的科技,而是我们的陪伴。
《智能》中,AI发出灵魂拷问:人类为什么值得被拯救?
人类不假思虑回答道:由于家庭、由于爱啊!
于是……
“We are 伐木累”这套说辞,AI听了都直摇头——毕竟它们可被投喂了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用以剖析人类的行为,由此产生对人类的失落望,倒也形成了逻辑闭环。
因此,《智能》与其说是在讲AI叛变,倒不如说,是在借用AI之口,反思在近些年数字化浪潮之下,科技该如何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又当何去何从。
我们不能再将技能视作纯挚的工具。虚拟与物理天下的人际交往、事情法则,形成了空前紧密的交融。
美好的生发,势必伴随着问题的凸显。然而技能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的问题。将统统甩锅给手机,显然是一种躲避。
△ 虽然AI想弄去世我,但是它说得好有道理
人类很糟糕,是问题的发明者,但同时更是问题的办理者;
人类很薄弱,但正是被挂在嘴边说腻的“爱”,证明着人类独一无二的存在,于困境中迸发出机器都无法预算到的可能。相信技能、相信人类自己,便是相信希望。
万物之中,希望至美。
- END -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