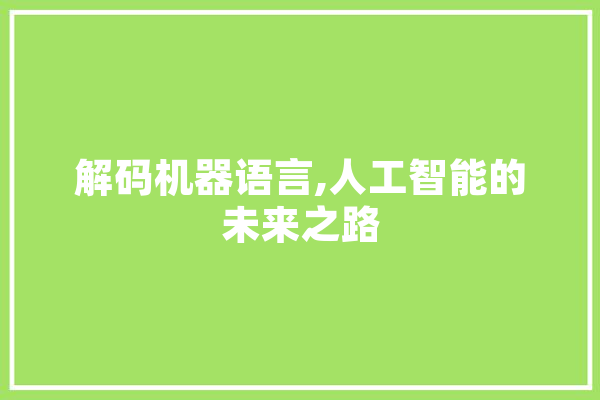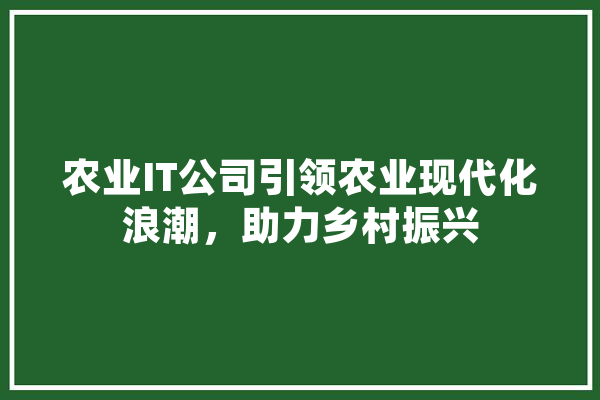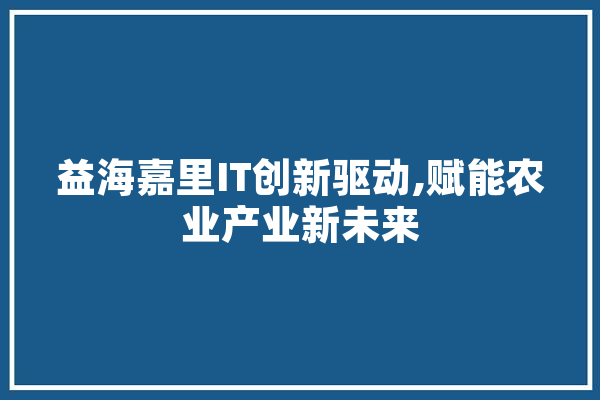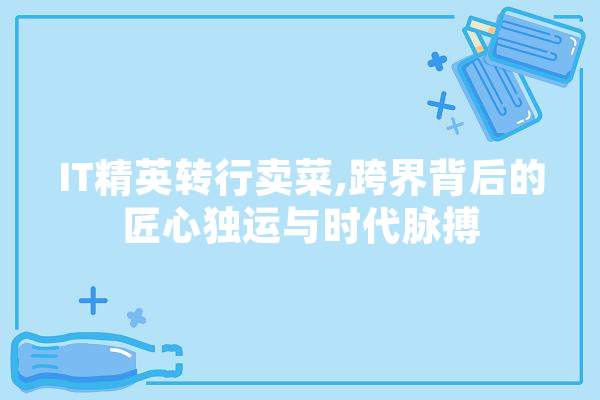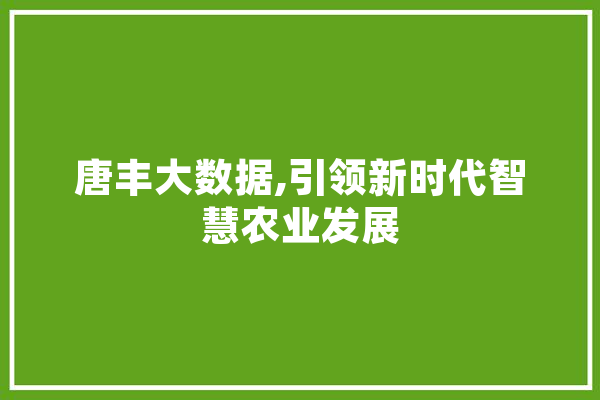农业劳动变迁:从刀耕火种到机械化 未来会彻底摆脱体力劳动吗_机械_农业
随着社会的变迁,本日的农业劳动,早已经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样子容貌,技能进步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也正在改变着农业生产的样子容貌。在更久远的未来,农业生产中,人类是否真的能完备摆脱体力劳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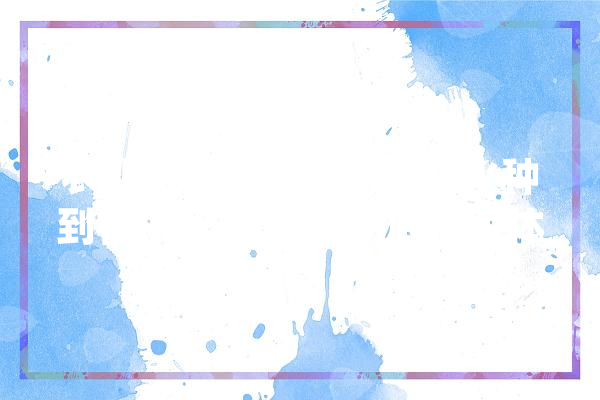
哈尔滨一处农田里,耕地机正在作业。新京报 王颖 摄
“耒”和“耜”背后的经济革命
人类可靠的农业生产,最早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在此之前,石器时期的出土文物显示,人们的生活来源更多依赖采集和佃猎,这使得原始社会的人们,生活总是流动不居的,他们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流落和迁徙,探求自然物产更丰富的地方。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冯开文先容,“在渔猎时期,人们的劳动效率是非常低的,尤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口增加,自然环境中的出产不足了,可采集、佃猎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们须要找到新的食品来源,最早的农业涌现了。”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冯开文。受访者供图
冯开文讲述一个农业史中广泛流传的故事,大约在8000年前,两河流域的人们开始把稳到,常常撒尿的地方,成长着一种分外的植物,它会着花结果,果实可以吃。“它便是小麦,在这个期间,人们开始故意识地留下部分小麦种子,并栽种它,来年可以收成更多的小麦。为了收成小麦,人们不再流浪,开始定居下来,最早的定居农业涌现了。”
稍晚一点儿的时候,在地球另一壁的中国,涌现了河姆渡文化,这也是一种定居文明,考古学者在河姆渡遗址中创造了水稻,这解释,此时的人们,已经在栽培水稻了。
刀耕火种,便是这个时期的写照,有学者剖析,刀耕火种,是一种半定居的农业生活办法。人们在点火肥沃的草地,用木棍在地上插出一个浅坑,把种子种在地里,不除草,不进行田间管理,等到收成时,用石制的镰刀收割。镰刀是一个很故意思的农具,在它涌现的时候,就基本上定型了,石器时期是那样形状,到现在,还是那个形状,只是材质不同而已。刀耕火种的模式是不可连作的,每年换一个地方。种过的地,等到重新长出草,再次肥沃后才会再种。
翻地工具的涌现,是一次垦植办法的变革,标志性的农具“耒”和“耜”,它们都是用来翻地的,翻地意味着连作,每年在同一块地皮上的劳作耕种,人们也开始真正定居下来。
江西新干县一对老夫妻在利用传统打谷机。新京报 王巍 摄
“这便是第一次经济革命,关键的标志是定居农业,”冯开文说,“这一阶段,中西差别不大,大都创造了类似的农具,类似的劳作办法。其紧张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在延续原始社汇合体劳动的同时,涌现了私人劳动,即个人化的劳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块地的垦植,另一个是涌现了分工,在集体劳动中,有人翻地,有人锄草,有人播种,分工涌现了。”
铁犁造就“男耕女织”的田园
大约在春秋战国期间,传统的奴隶制逐渐崩溃,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涌现。
“铁器在农业中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改变了农业劳动模式,”冯开文说,“铁器是工具材质变革的一个关键点,从石器到青铜器,变革实在不大,一方面,青铜器大多用在敬拜、军事等领域,很少用来制作农具,另一方面,青铜器脆,碰到石头就碎了,并不实用,一贯到铁器涌现。”
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两千多年的韶光里,铁器一贯都是农具的主流,没有其他材质可以替代。冯开文说,“铁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它更坚固、锋利,韧性也更好,这为畜力的利用供应了根本,在牛身上挂上石犁、青铜犁,都是不现实的,但铁犁可以。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一方面使得人类的劳动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出产的增多、新利益的涌现,也导致了社会革命。我们熟知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实在都可以看做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同一期间的欧洲,大平原的地貌为铁器的利用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更大程度地发挥了铁器的浸染,冯开文说,“欧洲中世纪利用马拉重犁,乃至有的用三匹马拉犁,劳动效率非常高。范例的案例,便是英国这个小国,在短韶光里成了欧洲的粮仓。”
此时的劳动是什么样的呢?冯开文先容,“家庭生产成为紧张的生产办法,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者,成为稳固的劳动构造。在中国,除了一小部分自耕农之外,地皮大多是地主的,人们作为佃户或长工,但他们也是家庭式的劳动。男性耕地种田,女性纺织、操持家务,也便是男耕女织的劳动模式,这种模式一贯持续到当代。在欧洲,劳动的紧张群体是农奴,但他们也因此家庭为单位劳动的。”
被蒸汽机冲破的田园
不过,无动力机器,也便是传统农具的改良,是有上限的,不论是可以灌溉千百亩农田的翻车,还是更省力的曲辕犁、更前辈的人力纺纱机,都没有冲破这一上限。“两千年封建时期,总是循环循环,和生产力难以涌现质变是有关系的。”冯开文说。
一贯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农业劳作办法,都没有太大的变革,老农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人力或者畜力,在地皮上垦植。汗滴禾下土,是农夫们辛劳的写照。
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的涌现,第一次改变了这一局势,冯开文说,“就像武器从冷兵器变为热武器,农业也是,蒸汽机、水力机器的利用,改变了农业劳动的模式。人们第一次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是部分,也深刻地改变了全体天下。英国的圈地运动,便是直接的结果。”
工业革命后,第一次涌现了工厂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人们也从传统的农人转变为农业工人,当代农业自此肇端。在中国,晚清时期也已经涌现了类似的模式,比如晚清状元张謇,人们熟习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但实际上,他还创办了农业生产公司——南通农技垦殖公司。在那个时期,中国涌现了很多经营地主、富农经济体等,但并不彻底,他们雇佣农人,但并没有完备把农人变成农业工人,这些农人本身还会为自己的地皮垦植。当时的主流,也还是家庭生产,铁犁、翻车、镰刀也还是紧张的农具。
一贯到新中国成立往后,农业机器化的进度才开始加快。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农业机器化的遍及,大量大型、中型的农机,涌如今华北、东北、两湖等平原上。此时的农机,早就不是蒸汽时期的机器了。
全程机器化不但是提升效率
2020年6月,北京房山石楼镇,大片成熟的麦田中,收割机收割、脱粒一体完成,脱粒后的小麦被直接装入货车,运送到粮库中。
房山石楼镇,正在机器化收麦子。新京报 王颖 摄
在全国,类似的场景到处都有。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机器化率达到71%。个中,小麦达到95%以上,水稻玉米分别在85%以上和90%以上。
在石楼镇,种地的村落民们,已经很多年不下地干活了,从翻地到播种,到撒药,再到收成,全程由专业的做事军队完成,他们只要付出每亩每次数十元不等的报酬即可。他们仍旧是农人,却不从事农业劳动了。
相对应的,开收割机的做事者们,成了新的劳动者,他们或者加入农机做事公司,或者自己投资购买农机,每年农忙时,开着机器,横跨上千里,乃至数千里,给分散在各地的小庄家们,供应机器化做事。一辆中型的机器,每天完成数百亩麦田的收成事情。
河南南阳,麦客来收麦子。新京报 王巍 摄
机器化改变了劳动模式,小庄家不再进行体力劳动,从事社会化做事的新时期“麦客”,同等面积的事情,劳动量也比传统的人工生产小了很多倍。
农业屯子部南京农业机器化研究所研究员陈永生见告,“机器化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提高近30倍,亩均节本增效500多元。”他说,“举例来说,靠人力种一亩水稻,从翻地到播种到收成,大约须要7-8个人工,也便是1个成年劳动力持续事情7-8天,但全程机器化,可能连1个工都不到”。
陈永生先容专为大跨度大棚设计的翻耕机。新京报 周怀宗 摄
智能种地会实现吗?
随着机器化的推进,大数据,智能设备,越来多的新技能、新产品被利用到农业生产中。更多人逐渐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以前,曾有人以为中国不适宜机器化,由于山多平原少,但现在,很多丘陵、山地都有机器作业,由于机器小型化了,”冯开文说,“自工业革命之后,技能的更新速率越来越快,一波又一波的新技能、新机器在不断被研发出来。在未来,那些原来以为困难的事情,可能都不以为是困难了。”
2021年4月28日,中国农科院的一处实验基地中,专门开拓的农机,可以在塑料大棚中自由作业,完成机器化深翻、起垄等事情。
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的机器化,一贯都是难题,蔬菜的种类多样,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特点,标准化、机器化比粮食作物更难。
蔬菜大棚机器化是未来探索的课题。新京报 周怀宗 摄
温室大棚中温度、湿度很高,而且空间每每相对狭小,劳动非常辛劳。长期处在湿热心况中,也随意马虎危害身体康健,造成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
但随着技能的进步,蔬菜的机器化也在快速推进,陈永生见告,当前,部分蔬菜品种的全程机器化已经可以实现,“比如南方较多的鸡毛菜、茼蒿等茎叶类蔬菜,已经有了一些方案和相应的设备,可以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器化。目前正在推广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难题正在办理当中,比如规模化的问题、比如地皮环境是否适宜机器化的问题,比如标准化栽种、社会化做事的问题等。未来办理了这些问题,蔬菜的机器化水平,一定会有一个快速升高的阶段。”
那么,在更远的未来,农业生产中,人类是否真有可能完备摆脱体力劳动呢?冯开文以为是有可能的,“确实,当前的机器化也有一些技能问题尚未办理,比如大田作物机收成时的摧残浪费蹂躏问题,比如分外地形、环境中的机器化问题,但技能的发展很快,在未来,未必不能用技能的进步办理这个问题。”
陈永生对此更乐不雅观,“完备摆脱体力劳动,这可能意味着连驾驶农机的人都不须要了。也便是聪慧农业,完备智能化生产,人们设计好程度,设定好参数,机器就会自动采集数据,进行相对应的作业,播种、浇水、施肥、收成,都是自动的,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实际上,现在我国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考试测验了,建立少人或者无人的农场,依赖智能设备光降盆。当然,现在干系的技能还不成熟,但未来总是会成熟的。”
新京报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正 柳宝庆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