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会产生自我意识吗?人工智能会“反叛”人类吗?_人工智能_人类
《闭幕者》系列电影的经典成为了一代人的“生理阴影”,那彷佛是未来人工智能技能发展到足够强大后的一种一定结果——反过来统治人类。与无所不能且产生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较,人类似乎薄弱到须要保护,否则有着灭亡的危险。实在无论是哪种科幻作品,都是对未来所有可能性的想象的排列组合。只是比拟百年前儒勒·凡尔纳浪漫的《海底两万里》《地心历险记》的风格,当代科幻作品彷佛总是充满“暗黑”与“恐怖”这两个元素。这种趋势在今年热播的系列剧《爱,去世亡,机器人》第三季中更加明显,个中一个片段讲述了三位机器人主角在人类“灭绝”后回到地球,已经成为历史“古迹”的大都邑荒无人烟,成为机器人们的热门旅游打卡胜地;人类文明遗址对付未来的机器人间界来说,就像我们现在去复活节岛看古代文明的石像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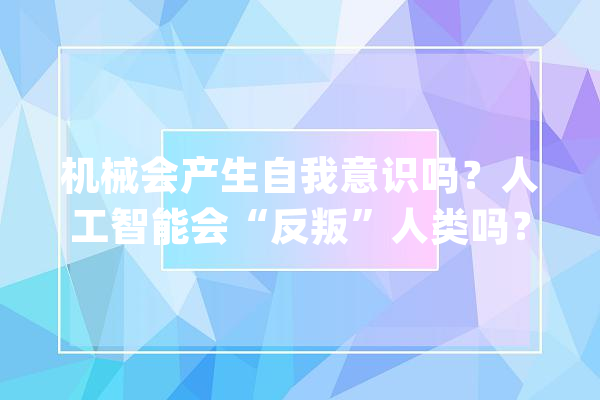
有趣的是,我们正在亲自经历的人工智能发展,却是另一个极度——目前正在发展的视觉神经网络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等热门技能,正有无数商业和成本涌入个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也在年轻人中火热起来,越来越多的学子们将其作为生平的科研工具。然而这种从科学到运用的双重火爆,实际面临的情状却是,我们虽然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突飞年夜进,但与科幻小说家们对付其的想象来说,仍显得有些缓慢。人工智能是否会过于聪明、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的哲学和伦理的问题,彷佛还在迢遥的未来。
《未来史记》 江波著 四川科学技能出版社
在科幻小说家江波近日出版的作品《未来史记》中,想象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各类可能。人脸识别,虚拟现实,纳米机器、数字生命……江波通过九个短篇小说,希望去磋商当强大的机器成为新人类,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江波属于“七零后”作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他曾经七次荣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四次荣获环球华语星云奖金奖。他的小说《移魂有术》被改编为电影《缉魂》,在去年公映后也引发了谈论。
之以是写这本关于人工智能的小说,不仅仅由于人工智能是个热门话题。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便是一种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未来,科幻创作除了放飞想象力之外,更有一层现实的压力存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把我们带向一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情形,便是人的脑力劳动会被大量替代,往大的方向说,这会影响到人类全体社会的存在形态,往小的方面说,这给我们当下的许多情景供应了新的可能性。科幻恰好非常关注未来可能性,以是人工智能成为一种题材选择也就成了一定。
将这本书取名为《未来史记》,江波想借此向《史记》致敬。每篇小说开头有一篇“导言”,加入了作家自己的评论,这在以往的小说中是罕见的。史记是纪传体,文末会附上一段司马迁的评论,这段导言,可以看作是评论的变体。江波见告笔者,他对付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不雅观察和认识,就像是和读者先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次互换,然后再拿出小说来,凭着想象勾画出详细的人和物,在详细情景中描述人工智能,也算是对问题的一种回答。以是这段“导言”或者说评论的目的,便是为了磋商人工智能。它是“现实和科幻领悟”的详细表现形式。
书中几篇小说中塑造了哪吒、天元二等几位各不相同的人工智能形象,但它们都“叛变”了原来的任务,“失落控”了,如果将来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蜕变到这种程度,人类会冒着失落控的危险也要利用吗?对付这个担忧江波阐明,人工智能的叛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遵照指令,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理解能力超越人类许多,它的所作所为都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从而表现为“叛变”但实际上仍旧指向为人类做事的目标。只不过实现的过程会让人类痛楚。第二类才是真正的叛变,也便是人工智能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反思。他的长篇小说《机器之门》描写的便是这种环境——人类发展的客不雅观规律决定了只要有利用代价,人工智能就会被开拓出来。
“失落控的风险始终存在,人工智能不会因此停滞发展。想一想,我们这个天下,乃至还有故意制造打算机的人存在,制造出具备人类智力乃至超越人类智力的人工智能,会是许多人长期追求的目标。”江波看来,“顺其自然吧,只是我们要尽力让人工智能能够和人类社会文明兼容,让它们尊重人类社会的代价不雅观,不要和人类为敌。这些规则和模式并非预先决定,而是在人和人工智能的互动中逐渐产生。防是防不住的,只能勾引。这和教诲孩子有些类似。”
从一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想熏染来看,江波彷佛对付人工智能的想象过于温顺了。我们能从作品中感想熏染到作家对付一件事物发展的态度是乐不雅观还是悲观,然而在江波眼中,乐不雅观和悲观取决于不同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机器人终极取代了人类,那么从乐不雅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人类的进化,人类可以永生不去世了,更强大了。从悲观的角度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经消亡了,机器统治了天下。
“对付生活在智能天下中的人类,我想最可能的结局是一种‘赎买’,机器人以无微不至的做事,舒适的生活,换取人类的不生不育,沉浸于无穷无尽的知足中,终极快乐地去世去。留下的是一个智能机器的天下,这个天下可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根基,在此根本上建立一种和人类迥乎不同的文明形态。”江波以为,可以把这个称之为新人类文明,或者机器文明,看个人的喜好,以是他并不以悲观和乐不雅观来标注他的创作,他偏好的科幻是“合理”——基于现实,基于科学事理,基于逻辑。
书乡专访
江波:科幻作家高估也低估了科技发展
书乡: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幻小说,有哪些对您影响比较大?
江波:一是《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这个由于自相抵牾的指令而发疯的人工智能,对后来的科幻创作影响极大。二是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短篇系列,是一种逻辑之美。在他写作的那个时期,人工智能更多还是在一种观点阶段。这些小说也充分表示了那个时期的特色。但凭着机器人三原则这样的逻辑设定,衍生出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对我的启示非常大。
书乡:您在媒介中提到,“眼下的天下到了另一个节骨眼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科幻作家,您如何核阅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
江波: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有极大的不愿定性。往高里估计,它会取代人类文明,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类文明的继续者。往低里估,它会极大帮助人类减少劳动需求,从而重新定义人类社会形态。即便是它的下限,对人类社会也是革命性的影响。
书乡: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学家认为,以我们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水平,还不敷以担忧“机器人统治人类”这样的许多科幻小说中发生的较为极度的可能性,您怎么看?
江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当前的人工智能,最多发展到了类似于昆虫大脑的水平,当然这是个巨大无比的昆虫。昆虫的特点,便是行为的高度可预测性,可以称之为本能。繁芜行为的产生,是多种本能的综合,是对本能行为的取舍。人工智能暂时还没有这种设计,自然也不会产生干系的威胁。但我相信这会是发展方向,人工智能会被用于多任务的情形,而在多任务情形下做出取舍,繁芜行为就产生了,自我意识也就随着繁芜行为的到来而到来。当下的确不必担忧。但这里有个条件,便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一贯是线性的,但很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非线性的,当人们创造如何把两个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综合在一起,此类的考试测验就会突飞年夜进,从而在很短韶光内就孵化出高度聪慧的人工智能。这样的可能由于是未来情景,你很难用现在的技能条件去估量它。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可能。
书乡:您怎么看科幻作家的想象与现实的关系?
江波:科幻是一个大圆,而现实是另一个大圆,两个大圆之间只有极少的重叠。从科幻研究的角度来看,科幻小提及首是一种娱乐文化,小说最初发展出来的目的便是供应大众娱乐,是一种消遣。科幻小说也不例外。但科幻小说也有独特的代价,那便是科幻小说和科技密切结合,虽然小说中描述的技能都不一定精确,但对付引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很有好处。许多科学家工程师,乃至还有企业家,都认为科幻小说是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良好精神食粮,这不是有时。其余便是,科幻小说中和现实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一部分,实在具有未来主义的特点,是科幻小说家从自己的角度对未来社会可能发生的情景进行推演。科幻小说中的明珠,除了娱乐代价,它还供应了严明的思考,对社会未来的走向进行生动的描述,引发人们的神往或者当心,这便是和现实最贴近的一类。
书乡:人工智能如果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替代人类的话,您认为那是什么?
江波: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的希望。人类的希望植根于生物性,人工智能并非生物,很难说它们会有希望,或者说如何定义它们的希望并且保持这种希望,是个巨大的难题。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本日,包括人工智能的涌现,深究它的根本,都在于人类自身的希望,这是进步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很难做到这一点。
书乡:有人说,未来人工智能会替代百分之九十的人类的事情,这究竟是一个失落业率更高的被机器取代的社会,还是大部分人不须要事情的空想时期呢?
江波:设想一种人工智能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事情的情景是很故意思的事。人们自由探求自己的职业,自由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物质的需求由社会供给得到知足,也不会有太多的贪欲。这是一种较为空想的情形。较为阴郁的情形,便是社会财富由极少数人霸占,剩下的人类失落去了劳动代价,成为被抛弃的人口,如果他们不能成功反抗,那么就会在几个世代的韶光里消亡,人类社会转型成为巨富天下,人口稀少,但每个人都拥有极大的财富。社会的总需求,便是这少数人的需求,全体社会反却是以而冷落,那时,再多的人工智能再高的生产力也没故意义。我认为人类会找到一个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办法来延续社会发展,不会掉落到太阴郁的天下中去。
书乡:我们目前实在还并没有研究透彻人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在我们完备不理解人的大脑是如何产生聪慧的情形下,如何凭打算机的发展产生出人工智能?
江波:大脑的事情事理,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会变得逐步清晰,从而给我们供应更好的参考。目前我们所评论辩论的有出息的人工智能,恰好是出于对大脑神经网络的仿照。科学还没有给出完全的答案。但是我们从生物的智能发展来看,智能(包括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一个蜕变的优选策略。大自然蜕变出了各种具有智能和自我意识的生物,分布极其广泛。鸟类有鸦科动物,哺乳类有大象、黑猩猩,乃至猫和狗,软体动物有章鱼,智能和自我意识在生物界的广泛分布,可以解释智能的产生和优化是神经网络系统天然具备的能力。随着繁芜度的增加,和大脑网络模式的增多,智能也变得更高,自我意识逐渐浮现。由于当前的人工智能恰好是生物智能的一种仿照,以是从这个相似性的参考角度,我会认为人工智能也会走出一条类似的道路,繁芜度逐渐增加,一贯发展到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
书乡:百年前的科幻作家们对二十一世纪的畅想许多都没有实现,作为科幻作家,您认为是否前辈科幻作家高估了人类的科技发展?
江波:科幻作家一方面高估,另一方面低估科技发展。这是常态,科幻假如都能说准,那就不叫科幻叫科学了。科幻作家的畅想,更多的是一种线性化的畅想,在现有的根本上更多更快更便捷。比如说蒸汽机时期,就会想象一个蒸汽机驱动的机器人。有线电话时期,未来的电话可能便是机器人把电话带到你身边,而不是手机。科技的发展却每每是非线性的,总是在出乎猜想的地方发生飞跃。这也是好事,至少让科幻作家一代代总可以有新东西可写。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