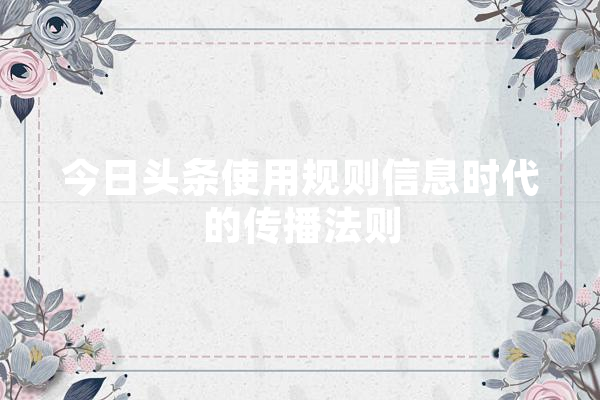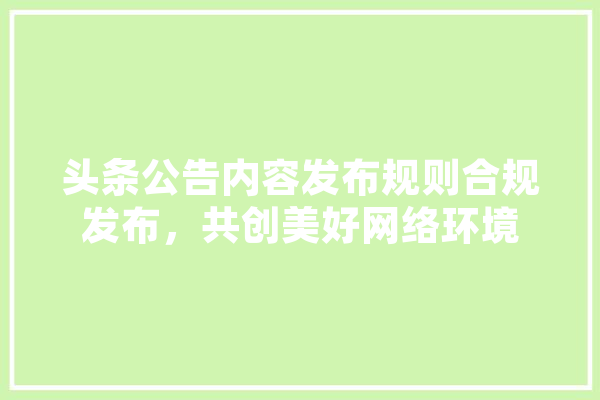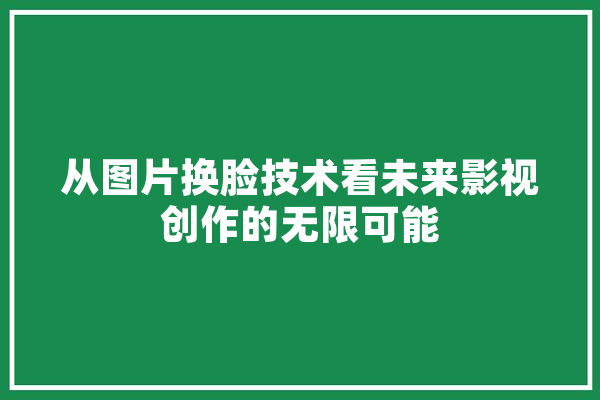公民网评:“人脸识别第一案”终审判决意义不凡_小我信息_特点
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迎来了终审判决。被告杭州野生动物天下被判删除原告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色信息和指纹识别信息,并于讯断生效之日起旬日内履行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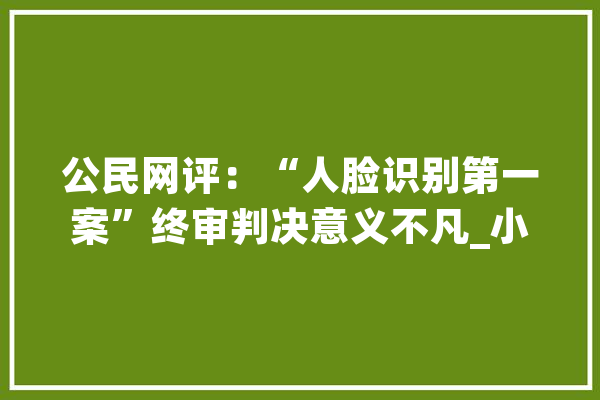
2019年4月,郭兵支付1360元购买野生动物天下双人年卡,确定指纹识别入园办法。2019年7月、10月,野生动物天下两次向郭兵发送短信,关照年卡入园识别系统改换事宜,哀求激活人脸识别系统,否则将无法正常入园。但是,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不同意接管人脸识别,哀求园方退卡。
这正是本案庭审的焦点所在,即对野生动物天下网络利用人脸信息的行为如何评判的问题。
不可否认,人脸识别是我们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进步技能之一。它所依赖的,是每个个体的生物特色,比如虹膜。这是与指纹、掌纹、静脉一样的生物特色,也被称为“人体密码”。与数字密码不同,生物特色是人无法改变的生理特色,是人的末了防线。这种主要性,恰如二审法院指出的: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表示自然人的生理和行为特色,具备较强的人格属性,一旦被透露或者造孽利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不测危害,更应谨慎处理和严格保护。
顺延这样的逻辑,去动物园看动物是不是必须要“刷脸”呢?显然不是。一方面,郭兵在购票时双方约定的是指纹识别,提出“人脸识别”是动物园的单方方法;另一方面,“人脸识别”也不是看动物的必要条件,而所有个人生物信息的采集必须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对付个人信息有明确的保护哀求。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就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须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该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造孽网络、利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造孽买卖、供应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刑法也规定,不经赞许而造孽获取,或者将合法取得的个人信息***或供应给第三方,此类行为均涉嫌构成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只不过,由于人脸识别等新技能的快速推广和广泛利用,很多人对身边的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每每习焉不察,乃至习以为常。同时,不少企业和部门,也以追求效率为第一目标,故意或无意陵犯公民个人信息,范例的如各地售楼处的摄像头。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很多时候也只是勾留在纸面上。“人脸识别第一案”的讯断见告我们,可以年夜胆地向人脸识别说“不”。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原告郭兵曾在听证会上提出小区门禁不得逼迫用生物信息识别的建议,被有关方面采纳。杭州因此也成为在物管条例中全国首个明确禁止物业逼迫人脸识别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郭兵开启的“人脸识别第一案”,寻求的不仅是个体权柄的私力救援,也是对所有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积极提醒。
具有标志性的个案讯断,每每会成为法治天生正义的落脚点、法治不断进步的增长点。期待本案的“尺寸之功”,能够发挥影响性诉讼的示范意义,进而推动个案正义转向制度正义,让法律文本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