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媒行业被AI彻底颠覆人工智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_性命_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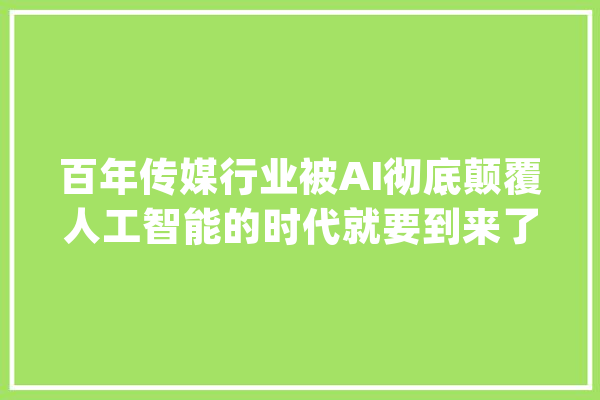
各位书友你们好,今晚我们连续共读《人类的终极命运》第三章,请大家带着以下问题完成今日的晚读:
1.你喜好讲故事或者听故事吗?
2.你知道人工智能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吗?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成为了全民热议的话题,大家在谈到未来的事情和发展时,都会不自觉地说:“人工智能来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类的灵感,让人们想到要去创造人工智能的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些玄乎。作者认为,是人类讲故事的能力催生了人们去模拟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机器。而个中最主要的便是故事中的隐喻。
比如我们说:心脏是一台机器泵。很显然心脏并不是机器泵,但心脏的功能和泵差不多,它像泵一样将我们的血液运送到了全身,以是我们就将它比喻成了泵。
通过这种想象,我们就把心脏和泵联系在了一起。这便是大脑的一种运转模式。
科学隐喻与技能每每是相互启示的,科学中的隐喻会促进技能的发展,而新技能的涌现又会催生新的科学隐喻。
大脑便是最好的例子。
自古希腊以来,至少有6次关于大脑的范式转换,这些转换不但关注大脑,也关注身体和生命,由于这三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有关生命的隐喻是泥土,无论是中国神话还是希腊神话,人类都是用泥土创造出来的。
这一隐喻源自于栽种与收成的农业社会,人们天经地义地认为:人类的生命自大地中生发。
泥土的隐喻促进了水力和风力的技能发明,而水力和风力的发明又启示了关于生命的另一个隐喻,人们不再认为生命是泥土,而是一具机器躯体,内含流动的液体。
那么,这一隐喻是如何出身的呢?原来,在水力和风力技能发明的同时,医学上创造了人体中有4种不同的体液,分别是:
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和血液。这种“体液说”的理论被2世纪的学者盖伦给继续和发扬。
盖伦认为,人就像一个繁芜的水力机器,人的行动是由体内的液体稠浊所驱动,心脏的浸染就像泵,勾引血液系统一直地循环流动。
盖伦的思想表现为人是自动化的水力机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为生命可以用机器表现的科学思想。
当希腊工程师利用风雅的水力机器,展示了机器人的生命事理。在这个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故事:
机器人的生命和运动,是液体的流动所驱动。当发明了更多的自动化机器时,生命的隐喻也就由泥土变成了流动的液体。
当一个会说话的铜脑袋的故事开始流传时,新的生命隐喻又出身了。
人工智能的发明者之一,麦卡洛克引用道:“等到铜脑袋说话了,我们就成功了。”
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复制人脑的神经元,来人造大脑。
哲学家笛卡儿根据铜脑袋的故事,创造了新的有关机器生命的思想,他假设人和动物的身体是一部繁芜的机器,骨头、肌肉和器官可以用齿轮、活塞和凹凸轴来代替。
于是一个新的隐喻又出身了,自动机器不再是水力或者风力,而成了机器,用弹簧和齿轮驱动。
笛卡儿不仅磋商了生命的机器隐喻,也开启了二元论哲学的辩论。他认为,天下是由“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两部分组成。
物质实体是指看得见的物质,而精神实体则属于隐形的非物质实体,比如思想和梦境。他推理出:在我们的感官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天下。
新的科学彷佛也在证明笛卡儿的二元论学说。科学家创造,天下上彷佛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浸染于物质,例如引力和磁力。
牛顿的引力定律学可以阐明统统征象,比如从最小到硕大,从地球到天体。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远间隔地发生浸染,让宇宙和行星都各安其位。
但是这种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彷佛只能别扭地假设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牛顿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将创造引力的实质任务,推到了未来大科学家的身上。
然而,在电场和化学等领域的新创造,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一起,又塑造了一种新的生命隐喻。
197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伽伐尼用去世田鸡做实验,他创造,当电流利过去世田鸡的腿时,田鸡的腿会踢起来。
后来德国生理学家雷蒙德,用电流计丈量动物和人身上的电流时,创造了电流利过神经流向了身体。
这些创造彷佛都在证明笛卡儿的二元论:有一种叫做“电”的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生物体内流转。
笛卡儿的二元论在化学领域也得到了佐证。化学家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化学反应:例如酸可以被分解后再合成。而烹饪蔬菜和肉类,却不能将它们再变回原样。
也便是说,无机的物质能够被反转,而有机的物质却不能被反转。于是化学家将它们划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
当时的化学家认为,生物体的组织能够有如此特点,是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发挥浸染。
于是关于生命之灵的想法涌现了,这种想法被叫做“生命力论”。
到了19世纪末,“生命力论”已经衰落,但二元论还存在。新的关于大脑的隐喻乃至还加深了二元论的存在。
显微镜的发展揭示了大脑中繁芜的脑细胞构造,这些神经元就像浓密的网络连接在一起。
科学巨人亥姆霍兹丈量了旗子暗记在神经纤维中通报的速率,他先容了一种关于大脑的新隐喻,他说,大脑便是电报。
到了20世纪40年代,打算机取代了亥姆霍兹的隐喻。第一台打算机被称为“电子大脑”,反过来,人脑也被比喻成打算机。
此后,我们就生活在了一个将人脑隐喻为打算机的时期。
新的隐喻将二元论的身心分离带到了新的层次。由于打算机技能硬件与软件部分天然分离,我们的人脑也被想象成这样的二元对立:
大脑的硬件是神经元构成的灰色糨糊,而软件呢,则是看不见的心智、思想和梦境等。
二元论理论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关于“大脑技能打算机”的隐喻中,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接管它,并思考该如何将心智编码到打算机中,以得到数字化的不朽。
从上面一系列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爱讲故事的大脑将生命的隐喻不断地蜕变和变异,一开始是泥土,之后是水和体液,然后是机器,再之后是电流,紧接着是电报和当代打算机。
我们创造,对付每一个隐喻,人类都曾设想过用自动的、人造的技能来支持这个隐喻。
人工生命变成了一种叙事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又催生了可以模拟人类和其他生命的机器。
隐喻指引着我们对人造生命与智能的思考,科学家们绝不疑惑,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更高等、更强大。
好了,本日的晚读到这里就结束了,通过本日的共读我们理解到故事的隐喻是催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头,来日诰日的早读韶光我们再见!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